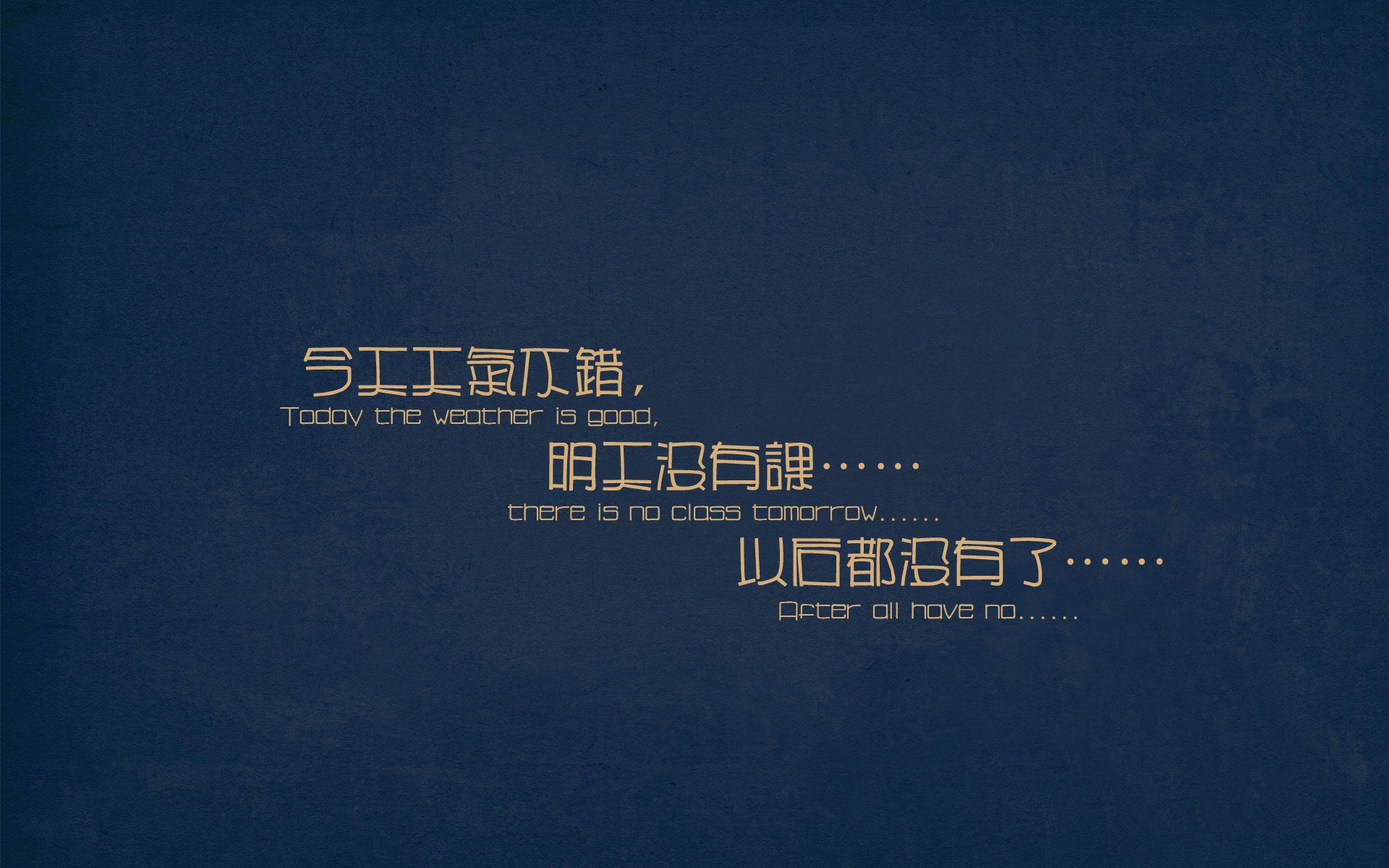陆建德谈枕边书
- 文化
- 14小时前
- 254
陆建德
陆建德:那时复旦外文系有好几位名家,我只听过他们的讲座,从未“师从”。英语专业的老师好几位都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比如系主任孙铢和教精读的曹又霖。曹先生不写论文,如果生活在当今,评职称就很不利了,但他是一流的教师,对文学作品的细节有着深刻的领会,他经常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作家这样写。教泛读的丁兆敏老师也是圣约翰的学生。疫情出现前,我如去上海,一般总会去看望她。当时陆谷孙先生还相对年轻,已经非常出名,可惜他没有教过78级的学生。复旦的《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是同类读本中的佼佼者。
中华读书报:大学毕业后您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多年的留学生涯带给您怎样的人生底色?在国外,您读得最多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哪些?
陆建德:徐志摩笔下的剑桥是浪漫化的,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不能忘记在剑河上撑船,因为我曾当着朋友们的面掉落水中。我感到惭愧的是曾经就读的学校成了一块招牌。80年代到剑桥去学习,实际上得益于我选择的研究题目,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资质,这是必须强调的。如果我当年想深入了解19世纪英国工人文学的状况,也许就去曼彻斯特或利物浦了,博士论文也许写得还好一些。不过剑桥确实给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化背景,我自己在那大环境下是无足轻重的。在那里的学习和生活肯定会在回国后的写作中留下印记,比如说我写过好几篇文章都与20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相关,收在《思想背后的利益》里。剑桥每个学院都有牛津的姐妹学院,互有来往。我所在的剑桥达尔文学院与牛津的沃弗森学院结对,而伯林是该院院长。英国知识界同情巴勒斯坦人,萨伊德在英国很受欢迎,我之所以对巴以冲突的历史感兴趣,也是受了英国环境的影响。我做的博士论文跟英国浪漫派诗人有关,法国大革命对这些诗人来说是一种考验,他们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为此我读埃德蒙·伯克的《论法国大革命》,折服于作者的雄辩。伯克看重文化的延续性,不相信抽象的自由,他通过批判法国革命力主明智改良的道路。我对伯克是有点倾心的,他和当时的激进派不同的是他希望修补房子而不是把房子炸毁。这种态度基本也贯穿了英国19世纪文学。伯克对传统、宗教和文化有一种与法国百科全书派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与伯林对启蒙主义的分析有可比之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让我倾心,当时这两本书还没有中译本。是不是我后来试图以伯克的眼光来观察晚清的新政以致生出几分同情?这些看法是否可以理解为留学经验带来的人生底色?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您先后出版了《戊戌谈往录》《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是什么机缘进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研究和著述中您有何收获?
陆建德:我在留学时就萌生为林纾的《荆生》翻案的念头,但是没有集中精力来写关于他的文章。在我的英国文学研究和林纾严复研究之间是有联系的。伯克和林纾都希望社会的转型平稳顺畅,但是渐进的路比较漫长,并不容易走。两点之间最短距离是直线,但是直线型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并不一定总是会带来最好的结果。我相信曲折的道路是多方面对话、协商、妥协的结果,参与者竞争中有合作,能适当换位思考,有所坚持,有所放弃。不然就是零和游戏。晚清新政推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改革,它也是危险的,在那条路上急奔的马车自身不牢固,几个颠簸之后轮子就飞出去了。辛亥革命是一个过程,很多重要环节还有待细察,比如武昌起义的前奏四川保路运动。发起运动的士绅反对铁路国有,目的是不受监督地保有为了筑路而募集起来的资金。铁路没有进展,而公司的资金却被挪用、滥用。保路运动导致了四川政府的倒台,赵尔丰被杀。当初那笔钱到哪里去了?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围绕着筑路巨款有着极其尖锐的利益之争,我试图以有限的史料揭示真相。辛亥之后过了几年林纾严复等人被迫离开北大,一些浙籍教授在北大慢慢占了主导地位,他们在20年代中期鼓动起北京女师大学潮,少数激进学生其实有复杂的背景。最后这部分内容我会在一本关于鲁迅的著作中展示。
中华读书报:在国外读得最多的是什么中国文学作品?
陆建德:留学时当然也读中国书,包括有些当代小说和反响较大的论文,不过远不及英文著作多。1985年我读了史景迁作序的《干校六记》的英译本,译者是大名鼎鼎的葛浩文。这是我第一次读杨绛先生的著作,很为她克制的风格所触动,想不到回国后有幸成为她的同事。我读英国文学(含批评),可能还略略改变了我欣赏中国文学的方式。我博士论文写的是英国20世纪批评家利维斯,他对文学中的滥情现象非常不能容忍(观点未必正确),也许这是英国趣味使然。我读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时由女主人公范尼想起林黛玉,为什么她们两人身世很像,待人接物却如此不同。范尼能够承担起责任,而林黛玉却对自己的地位过分敏感。
中华读书报:您在厦门大学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怎样?
陆建德:我2019年去厦门大学,担任外文学院的讲座教授。第二年厦大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揭牌仪式,得到我国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界的诸位同仁的有力支持和热心鼓励。去年厦大举行百年校庆时中心举办“美美与共“论坛,吸引了学界的关注。去年11月中心的另一个论坛规模不大,议题“关于人性的想象”却别具一格。我作为中心主任一度隐隐感到压力,好在厦大外院的同事一心向学,教书之余勤奋写作,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的时候英语地位很高,明年外院将迎来建院百年纪念。
中华读书报:会为学生推荐书吗?
陆建德:这个问题一言难尽啊。我在厦大做过不少讲座,每次都会提及一些书。总的来说我希望学生养成广泛阅读的习惯,仅仅消费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是远远不够的。老师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学生对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慢慢成长为萨伊德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文学阅读有助于心智的成熟,但是那种成熟绝不意味着一种完成的形态,恰恰相反,它是包容的,时刻得到滋养,来自开放心态和细腻感受力的滋养。现在我们讲跨文化研究,前提是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人有可能克服差异,追求共同或相通的价值,玛莎·努斯鲍姆的著作是我乐于推荐的。
中华读书报:《自我的风景》收入您谈及莎士比亚、狄更斯,论及奥威尔、赫塔·穆勒等,见解都很独到,很喜欢您的文笔,从容、严谨、才华横溢。能否以其中一人为例,谈谈您的这些文章的形成?比如一般是阅读多久或几遍之后开始动笔?
陆建德:我想这没有定规,有的话题写得顺畅一些。我经常是读了某个领域一系列著作,最终却未能提笔写作,碰到了所谓的“写作者的障碍”,在某个地方卡住了,原因是多样的。在准备某一篇久久耽搁的大文章过程中,进入某个旁支,有所发现,很快就写成了副产品,而主要任务竟至渐渐弃之不顾。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电脑里就存有几个失败的例证。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学术研究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陆建德:我希望身上总能保有孩童一般的好奇心。也许学术研究最大的魅力就是好奇心不断受到刺激。求真的意愿以及对公正的渴望促使我们发问:某件事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当事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样公平吗?如果我的文章里隐隐显现出因这几个问题而产生的焦虑,那就是一点微末的成功了。我不大喜欢宏大话题,总是觉得细节才是精髓。穿透空泛词语的表象,有时会看到骇人的景象,完全出乎意料。
中华读书报:您主编过20世纪外国散文经典,也出版过《无界》等散文随笔,很想了解您对于散文经典编选的标准是什么?
陆建德:编选散文没有一贯的标准,郭宏安先生给我启发很大。他曾介绍斯塔罗宾斯基对蒙田散文的评价:“带着永远年轻的力量,出于永远新鲜直接的冲动,击中读者痛处,促使他思考和更加强烈地感受。有时也是突然抓住他,让他恼怒,激励他进行反驳。”我编《20世纪外国散文经典》时恐怕未能体现蒙田散文的高度,不过我也希望所选的文章以批判性见长,“击中读者痛处”。书编完后我是失望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别。假如差别还暗含着优劣的意思,那纯粹是我个人的偏见了。
中华读书报:如果去荒岛,您会带哪三本书?
陆建德:蒙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我读他的随笔(三卷)时却感到他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学问好,但是丝毫没有架子,善于以陌生者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自己古典学知识储备不够,读蒙田可以顺便补课。在英国文学史上,约翰逊博士是我特别敬仰的人物,鲍斯威尔的英文《约翰逊传》读过很多片段,但是还没有从头到尾读完,现在发配到荒岛,有约翰逊博士做伴是不会有孤独感的。第三本书是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纪念版)。唐代的长安在文化上是混杂多元的,吸引了不少来自西域的艺术家。我要用这部书来提醒我中国文化如何从交往中变化发展。郭沫若在30年代写过《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文章证明这位音乐家的音乐是“合成”的,“是新来的胡乐和旧有的古乐或准古乐结合了所产生出来的成果,也可以说是在旧乐的砧木上接活了新乐的苗条。新乐是通过了胡乐之输入期而达到了创造期”。近来我常说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互动,突出文化的交流和融通有利于克服一种狭隘的本质主义文化观。
中华读书报:最后咱们再谈谈枕边书?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陆建德:遗憾的是我那几本枕边书总是让我尴尬,让我记得无法完成的作业。有几本是陆游的传记(其中邱鸣皋的《陆游评传》最出色),还有他的诗集,很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诗人的复杂的面相。鲁迅不是很喜欢这位乡贤,为什么?在“民气”和“民力”之间,鲁迅更看重民力,不客气地坚持陆游的豪言壮语应该打折。还有一本是上世纪80年代集体编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这本书记录了上海现代化的进程。乔治·艾略特的英文原著《教区生活场景》(精装)是请学生买来的,还没有中文译本。
(栏目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