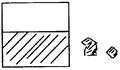来信乡愁里的大雁梦
- 旅游
- 40秒前
- 78
作者丨赵进斌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语文课本上的第一篇课文《秋天来了》,课文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我的故乡处在沭河、浔河两条河流包裹中三角州地带,是祖辈生存繁衍的沃土,河岸宽绰的黄沙土地上,白桦皮本地大杨树高壮挺拔,粗线条柳树婀娜多姿,苍桑的槐树、榆树翠绿清新、摇曳款款,还有诸如梨树、粟树、苹果、海棠、桃李杏等众多乡间寻常果木树簇拥林立,各展风姿;更有那松、柏、秋树苍翠庄重,杂树及灌木丛的争相缠绕扩展,一年之中大半时间,村庄整个被淹没在郁郁葱葱的绿荫之中。两条包裹村庄的河流一年四季河水清澈奔流,微波荡漾,各种各样的鱼虾成群翔游,蚌、蛤、虰螺云集迹行;河岸旁青草萋萋、各种野花争奇斗艳,芦苇簇拥,成群结队的水鸟傍飞,野鸭、鸳鸯戏水,沙鸥翩跹,秋天霜降季节到了,课本上的一幕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鸣叫着从北边天空飞翔而至,黄昏时分,在故乡河滩上空盘旋着降低高度,忽喇喇、扑喇喇落将下来;顿时河滩上、河水中,一群群大雁鸣叫悦耳声此起彼伏唱和回应……故乡这一幕幕曾经绿色原生态生动景象至今仍存留在我脑海中,不时出现在梦境里,浓缩成令我遥想绵绵、恋恋不舍的乡愁。
那时的故乡河岸黄土地中,各生产队种植的冬小麦的麦苗霜降后正盘墩窝叶成拳头大小,绿油油地铺展成片,对这些向南迁徙的大雁具有磁场一样的诱惑。我幼年、青少年时代,这种深秋大雁迁徙的固定场景总是定时出现、循环往复。我记忆中最早的印象是,从东北西北方向大雁群黄昏时节飞至村庄上空后,就鸣叫呼应着盘旋侦察,片刻,雁群有的直接就栖落到河岸上的麦田中,然后就纷纷迫不及待地低头啃吃麦苗,这时的嫩绿的麦苗,对以嫩草为食迁徙的大雁来说,是补充旅途劳累身体再好不过的食品。当时,生产队的大人们还心疼辛苦播种下刚盘墩的麦苗,怕被雁群啃吃后影响来年的收成,见如此多的大雁来啃吃,还不时地跑过去用手掷石块哄飞雁群。但这种策略很快就被雁群习以为常,它们往往从这块地一哄而飞到不远处另一块麦田,连绵大片湖田全是这种麦田,如此吓唬手法收效甚微。久而久之,雁群见人们不过如此,对自身构不成多大危险,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有时生产队社员们黄昏还未收工,它们便一群群络绎不绝地飞落到不远处的麦田地,迫不及待地大饱口福。这些迁徙的雁群并非只补充一天两天就飞走,它们大约在迁徙途中见到如此不愁吃不愁喝的地方也不太多,它们竟乐不思南,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十天半月的不飞走。白天它们聚集在河水三角洲中尽情嬉戏,晚上便飞上岸麦田中大快朵颐,其奈我之何?
造成社员们对雁群啃吃麦苗哄赶积极性下降的另一原因是,那时社员们家家户户都要养猪。大雁和家养的鹅这类飞禽被社员们称为直肠子货,囫囵吃囫囵拉。由于它们晚上都是成群结队宿营在麦田,啃吃的麦苗不一会就排泄出来,第二天一看雁群宿营过的麦田里,密密麻麻雁屎遍布。这种消化不良嫩麦苗的雁屎,又是猪爱吃的佐餐。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这个喂猪的窍门,在人尚且饥肠辘辘的年代,捡拾大雁屎能喂猪,很快便风行一时,全村男女老少,早出晚归背筐挎蓝到湖田麦田去捡拾雁屎喂养猪是那时每天的必修课。有些社员家将这些雁屎捡回放在缸罐里用水一泡成糊糊状佐料,喂猪时拌在糠末中,竟使得这些肥头大耳的家伙津津有味吃得肚皮滚圆。那时家家户户社员养的一头猪就是全家一年指望的固定银行,能将雁屎转化成极为稀缺的人民币,这个账目是傻子也能算明白的。于是,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就成为家家户户捡拾雁屎的主力军。为了捡拾多快好省,每日在河岸成片的麦田中寻找发现雁群屎多的地角、麦田,自然展开了起早贪黑的竞争。我清楚地记得,入冬的多少个早上,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正睡得香,便被父母催促快起来背筐去捡拾雁屎,因为去晚了就被其他人捡拾得没有了。再说社员们后来发现,过冬的麦田被大雁啃吃后,对来年小麦收成影响不大,所以社员们后来就基本上不赶哄雁群了。那时大雁之所以不太害怕人们,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萌生伤害大雁之心。我们在河边玩耍时,不远处大雁群里、鸿雁、水鸭子、白鹭等众多水鸟混杂一起,争相嬉戏,除非人有意识地靠近驱赶,这些飞禽是不会飞离的。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太长,文革期间,信奉伟大领袖战天斗地、其乐无穷语录号召的社员们发现日子越来越穷,生活的艰难让人把目光首先对准飞禽走兽。用猎枪、用网打野兔、各种野鸟,接着又听到是河两岸邻村有人用抬枪(一种打散铁砂的猎枪)开始打大雁、鸿雁、野鸭。他们先是选取雁群落在河边沙滩及水中最多的地方,挖出一个沙窖子伪装好,猎手们趁大雁不备时偷偷地趴进去,等候雁群半夜三更聚拢睡觉时,突然发出惊人声响,雁群在惊动惊叫中纷纷起飞,选取它们展开翅膀将飞未升起时,扣动扳机,近百粒的被火药烧红的铁砂出枪筒后成弧形散面射向这些起飞状面积最大雁群中。据说,成百的雁群这样一枪最多能打十几只大雁。雁群当场被打死的不说,被铁砂打伤后还能勉强飞起来的也不少;雁群惊魂丧魄地惊叫、哀叫声混杂在静夜中格外刺耳,令人不忍卒听、难忘。这一声闷雷似的枪响在黑夜里格外传得远。那时,社员们经常在半夜三更听到这样的枪响,接着,雁群们乱哄哄扑喇喇地飞舞声、惊叫声回响在村庄上空,大家心照不宣的知道,又有打大雁的。这个夜晚的黎明时分,就有不少社员早起到河边沙滩草丛里,去寻找那些被打伤后飞到近处掉下来的伤大雁,有些被发现后已经死了,有的还奄奄一息,有的竟还能飞出好远,直到被穷追不舍的人抓捕到。
就这样,白天村里不断地传说,邻村里的谁谁,拾到被打伤的大雁了,是又跑了一阵才打下来的……捡拾到大雁的人立马成为全村人羡慕眼馋的对象,走到哪儿都会被人夸奖、称赞,竖大拇指。
在那人人肚皮里的荤腥、油水极度稀缺的年代,拾到一只大雁,全家人一饱口福不说,其行为还为全村人羡慕,这种运气,对饥肠辘辘的社员们该具有多大诱惑力!
用不着谁来号召发动,村里青壮年、半大孩子,就自发加入到这个捡拾大雁强烈向往憧憬的竞争中。
那时我正好十多岁,我的捡拾“大雁梦”就此开始。
那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各县、公社、大队为早日使粮食亩产产量“跨纲要”、“过黄河、长江”,都号召广大社员利用早起晚睡空闲拾粪便。一时,人的粪便、猪狗的粪便,牛羊等走兽的粪便,由此成为香饽饽。为了完成队里下达的任务和指标,社员们早起晚睡背着粪筐捡拾走兽粪便是寻常事,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一大景观。早起社员捡拾得满满一筐,找到管理员称过,记上工分,晚出去捡拾的社员,捡拾粪便的概率便大打折扣,自然就完不成任务,免不了后悔着急。有的社员为了完成规定任务,甚至不得不到社员家猪圈内外粪汪里去偷也是屡见不鲜。捡拾大雁同时兼顾粪便和雁屎,一举三得。于是在社员中暗自展开三样捡拾的竞争。
虽然早出晚归者无不希望自己碰到死伤的大雁,但每次被猎枪打伤飞离后又落下来的大雁概率极小。一开始,我积极性相当高,那时家里没有钟表,估算时间以鸡叫声为准。鸡叫三遍,天就蒙蒙亮,不待父母催叫,我就起身,背起粪筐,直奔村西南。此时东方刚呈现出灰蒙蒙鱼肚白的状态,除了此起彼伏的鸡叫、零星的狗叫声,大地沉浸在静谧之中。按理说,一个十多岁的半大小子应是心里感到害怕,但捡拾到大雁的荣耀梦想已经压倒了一切。我几乎是快步奔向村西南大雁聚集的三角洲,先在河边崖下草丛灌木丛中瞪大眼寻找有无伤雁,兼顾粪便,一边寻找一边暗自庆幸——今天总算第一个来的,如果有死伤雁肯定是我的,脑海里已经设想着自己捡拾到大雁,那该是怎样高兴得无以言表的幸福场景……
正当自己精神高度集中,兴致勃勃地瞪大眼睛寻找时,迎面就碰到其他同伴或者大人,一个、两个、三个……都在沿着河边寻找,彼此心照不宣。后来一打听,有的同伴比自己来的还要早,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不免泄气。每次见这样,当天捡拾大雁的希望便如肥皂泡样顿时破灭,只好快步奔赴麦田,去捡拾雁屎喂猪,然后就背着粪筐垂头丧气地回家。
1 天、5 天、10天、半月,1 个月、3 个月——冬季束了。大雁飞走了,今年它们的迁徙结束了。明年、后年、又是一年。我和其他同龄人、社员们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种行动,每年捡拾到伤死雁的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只是在希望中重复着同样劳作,早起晚睡地圆雁梦。
多少个冬日顶严寒,踏霜冻,却连个雁毛也没见着。现实做不到,梦中却实现了。我有几次做梦,真是拾到了一个伤大雁,回家后父母喜悦表情,左邻右舍地夸奖,社员们指指点点地羡慕样子,让我得意忘形手舞足蹈、高兴得要死……醒来后又是南柯一梦,默然神伤。
捡拾被枪击死伤大雁,令我梦寐以求的梦想!
一晃几年过去了,历史和岁月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农业虽然仍是学大寨方兴未艾,社员们仍是被号召捡拾粪便,但全大队、甚至全公社的粮食产量始终在过“黄河”与“长江”之间徘徊不前,甚至还倒退到“纲要”边缘。
变化是有的,最先显现的是人们对付大雁手段,先是枪杀后是下药,随着“敌百虫”农药的使用,雁群一次被药死数量激增。在河流三角洲沙滩,有些人为了毒药大雁不择手段,竟在沙滩上特意种植冬小麦,用麦苗来吸引大雁。我曾在集市上看见吆喝卖大雁的,近20多只被药死的大雁,被卖主堆放在手推车篓中。这些人高声吆喝着:“哎、哎、哎,卖大雁啦,俗话说,能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斤啦……”当被问道“敌百虫”的药效时,“这药只药扁毛的”(飞禽),不药圆毛的”(走兽,人也是圆毛的)。我曾走近这些令我在课本上读到,一年年秋天,就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的雁阵飞降到村庄上空,在高空展翅飞翔盘旋悦耳鸣叫声中落在河滩上麦田里,曾经和人类近距离观看着的灰白色大鹅们——它们死气沉沉闭眼蹬腿被窝在一起,冷干的血水散落羽毛上;它们成群结队曾经多么生气勃勃、活灵活现,嬉戏、舞蹈,但它们永远也不会想到,人类会用砂子枪射杀,在他们爱吃的麦苗上喷洒上了敌百虫,令它们命断南迁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堆积在集市出售。
吃一堑长一智。每一次枪声都让雁群幸存者们刻骨铭心,曾经令它们心驰神往的河流,在他们眼里,那是这群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们布下的致命陷阱;那大片绿油油令它们大饱口福的的麦田,是让它们成群结队被斩草除根的毒药,一传十十传百,它们飞临这三角洲的村庄,飞临大片湖田麦田,不再留恋、绝不停留,而且斩钉截铁、义无反顾,告诫着、警告着、警示着、振翅高飞、继续南下。
于是,几年的功夫,我在小学课本上读到的景象,每年秋天都耳闻目睹的场景,令我心驰神往的梦境,逐渐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而且一去不复返。
我们捡拾雁屎喂猪的好处自此结束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是剧毒农药发明应用的高峰期,DDT、敌百虫、滴滴畏、203、1605、毒鼠强……这些农药毒杀性一种比一种剧烈,毒杀动物的时间越来越短,以至于出现“五步倒”这种超强毒药。这些剧毒农药几乎都具有隔代、几代的毒杀滞留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爬的、水里游的,很快消失、灭绝;花草树木凋零、枯萎。岂止是飞禽走兽、广大动物,在广大农村村民们,因纠纷、口角、谣言、谎言而喝滴滴畏、203农药自杀的事件曾经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如果统计真实数字,煞是惊人。
我的故乡,那几百年来形成的两条两条包裹村庄使得祖辈生存繁衍的清清河流,曾经四季变换颜色,蕴涵着生机勃勃,日月欢快地流淌,包容万物滋润万物的河水,永远充满着怀春柔情的她根本不会想到温饱后的人类首先蹂躏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五小企业(小造纸、小化工、小冶炼、小屠宰、小五金)遍地开花,曾经清澈的河流、池塘很快各种水生生物绝迹,水质变黄、变黑、发臭,紧跟着河岸花草树木、枯萎、凋零死亡,庄稼绝收……紧接着沿河村庄人们患恶性肿瘤死亡概率大幅上升。人们对大自然疯狂作贱、破坏、索取、榨取导致大自然循环报复,人类终于自吞自己造孽的恶果。
我是1979年底离开故乡到县城参加工作的,由于常回家看看,亲眼目睹故乡这两条河流被彻底污染二十多年,导致飞禽走兽、水生生物迅速灭绝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沿这两条河祖辈居住的村庄家家户户村民打的压水井水无法饮用多年,至今河流无法有效治理,我曾多次写信反映投诉到县、市有关主管部门,但基本是泥牛入海。我后来全家来到沿海城市。30多年来,曾经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莺啼燕语、桃红柳绿、蛙鸣鱼翔、芦白桑清、多姿多彩的青少年时代故乡情境,时不时令我梦绕魂牵。我不时回故乡,但故乡河流至今也未恢复到昔日的景象。我曾在深秋特意回家乡寻找课文情景,黄昏在河岸抬头仰望、极目远眺,但一次次失望而归。我对1980年上演的电影《归心似箭》主题曲《雁南飞》这首歌曲情有独钟,印象极为深刻,“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今日去原为春来归,盼归莫把心揉碎,莫把心揉碎,且等春来归……”是这首歌词由群雁南飞勾勒出的乡愁内涵深深打动我,每当这首歌曲旋律一起,故乡那深秋雁阵飞过,雁鸣声声情景交融,我脑海中就浮现出动人心弦的景象,令我遥思绵绵!
我知道,家乡父老乡亲们的正在上小学孩子小学课本中仍有《秋天来了》的课文,但文句已经“与时俱进了”,没有了我上小学时课文原句意,也就不可能看到在空旷蓝天、朵朵白云之间鸣叫盘旋的雁阵,更不可能在河流中见到嬉戏的雁群水鸟,自然就不可能产生我青少年时期抬头仰望、观看、极目远眺天空雁阵记忆的联想、幻想,令人遗憾的还有,他们看不到众多飞禽走兽的多姿多彩的生动有趣生活场面,也看不到乡间各种花草树木的摇曳多姿万紫千红四季变幻风景。他们每天都要被父母骑电动车送到镇上去读小学、初中,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就到县城上学。他们的记忆里,耳闻目睹的大都是灰蒙蒙的天空,不时断流干涸被挖掘得千疮百孔的河流中到处是垃圾、塑料袋,河道散发着难闻的污水气味。春天,河堤、沟、渠、岭畔,到处是千篇一律的速生杨树,漫天飞舞的如棉絮样的杨树花带来污染无孔不入,令人气恼、愤懑而又无可奈何;曾经是希望的田野上充斥遍布着一色白晃晃的塑料大棚,千篇一律地种植草莓、经济作物,日益衰败的村庄到处充满着冷漠、荒凉,男女老少对金钱极度渴望的眼神和表情……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成人走向社会后会是怎样的情景?
这难道就是多少年来美其名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你何日再现我小时读过、耳闻目睹过秋天课文的景象?何时找回我梦绕魂牵雁阵南飞的乡愁?
上一篇
陈忠康:我的临帖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