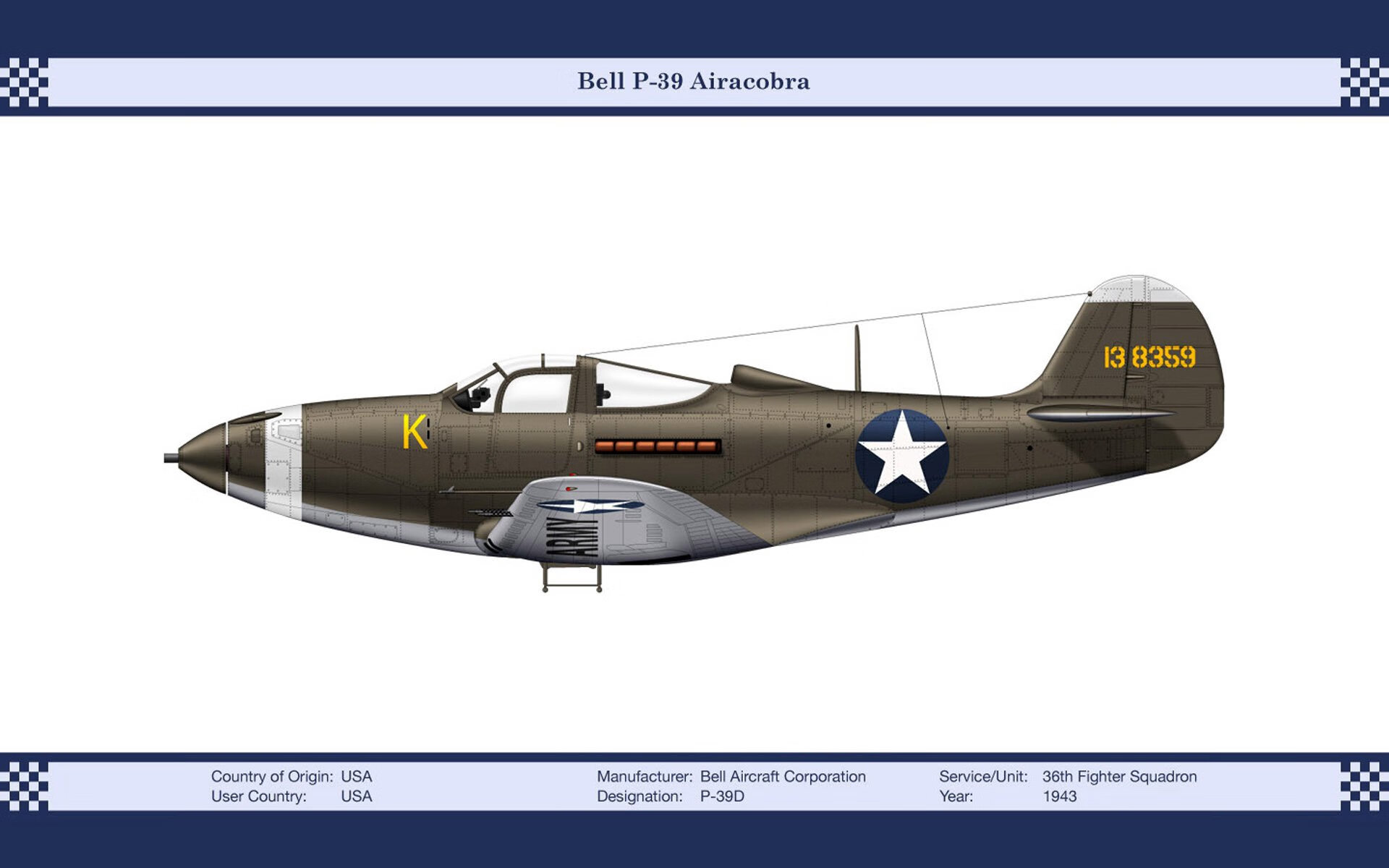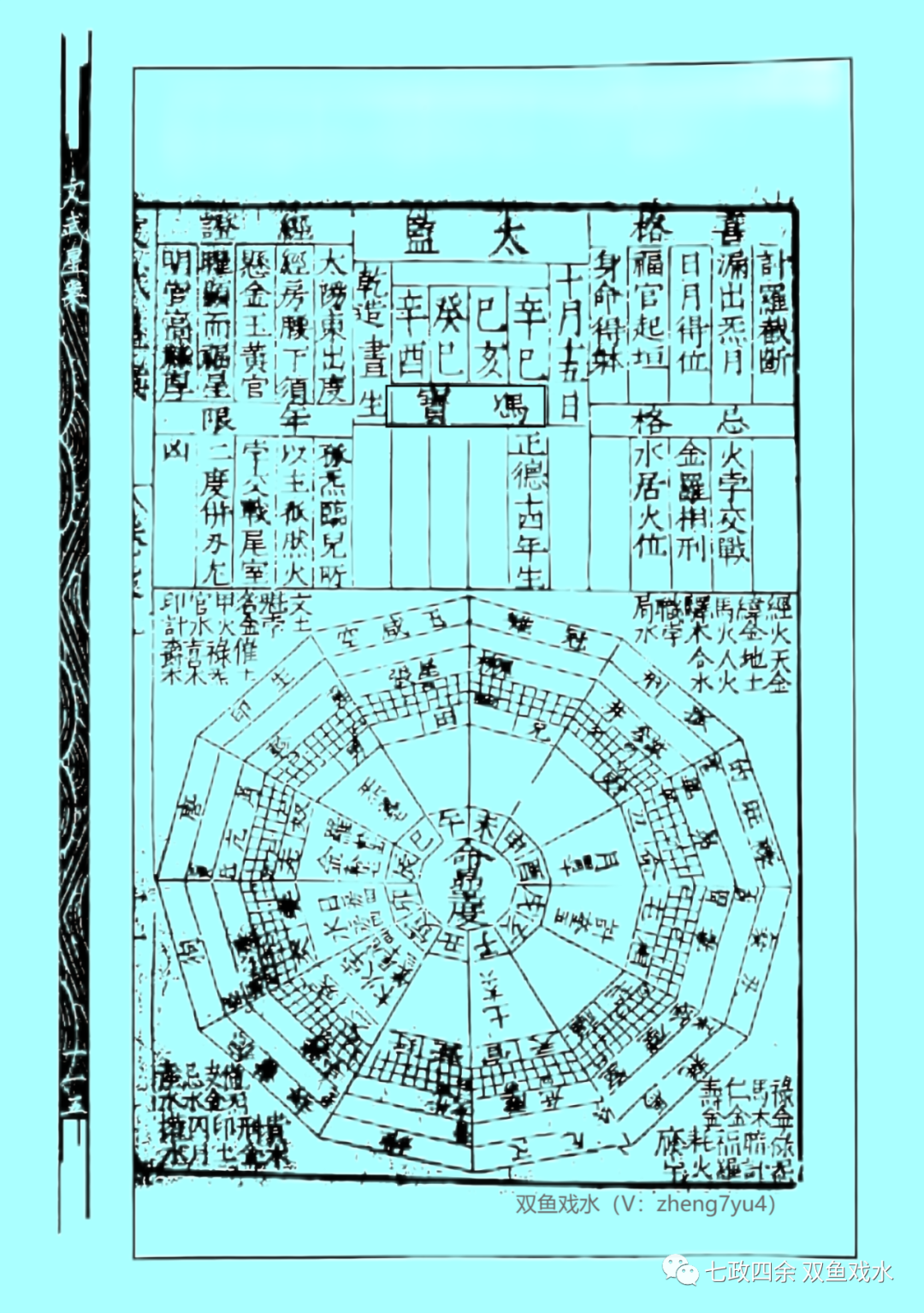新房子旧房子
- 社会
- 11小时前
- 333
新房子旧房子
文/蓉子
平哥家的新房建在小河边,青灰色的外墙,大气而雅致。从二楼望去,小桥、农田、新房、老屋尽收眼底。
近处的农田里旧房子,有村民在劳作。杂乱的田地被整理成一块块豆腐干状,有人往地里撒着种子,是花生。早春时节,水稻还没有开始插秧,花生大豆已先行种下。
河上的那座小桥,是伟的父亲在60年代带领乡亲们修建的。夏天,孩子们在这里嬉戏打闹,女人们在河边洗衣。丽子仍能清楚地记得,喝醉酒的父亲,摇摇晃晃从桥上走过,跟在后面的她心跳到了嗓子眼,却不敢去扶,深怕爱面子的父亲拒绝反而会掉进河里。如今,河水渐渐干枯,桥面斑斑驳驳,两边已有了岁月的齿痕。
河对面,新房与旧屋错落其间。新房贴着喜气的春联,旁边没了屋顶的旧屋,落寞孤寂。稍远处,就是伟家的老房子了。
他家的老房子,他父母亲一砖一瓦修建起来的房子,也坍塌了。
兀兀站在这堆已长出绿草的黄色土堆中,四周残垣断瓦,一片凄凉。家人从四周残留的墙面,依稀辨认着曾经的厅、房、灶、天井。那个堆满草的灶间消失了,房间不见了踪影,天井重归地下。哦,那两扇门,前门、还有那扇连着小巷的后门,那扇他的母亲时常站在巷口、呼唤孩子们回家的门,还站立着。告诉他们,这里面就是家了。
我仿佛又看到了它初见时的模样。
前门的厅是连着灶间的,中间的天井四周有廊,廊边是房。第一次住的那个廊间,印象极深。农村的房间都是两层的,小阁楼可以储藏谷物。那个晚上,一整晚,都听见老鼠在楼板上操练,像撕纸的声音。从这头撕到那头,再从那头撕到这头,用棍子戳戳楼板,停了;等一躺下,操练继续。它一晚上不睡觉的撕那玩意儿干嘛?
对于他们姐妹,这座老房子,那些愈来愈远的往事,像飘渺的梦,久远,但难忘。
担任大队书记的父亲,话虽不多,可不怒自威,大伙都怕他。堂哥得了部收音机,兴奋得不行,一个人关在房间捣鼓着。窗外一个身影闪过,他知道是叔叔回来了,音量关小,继续玩着。再一会儿,身影又从窗前经过旧房子,心一颤,他不敢再听,连忙关了收音机。他可不想惹怒叔叔。
铁汉柔情。灶台边,父亲流着泪,在炉火的映照下看着儿子从前线寄来的信,他担心儿子的安危。但做为村镇干部,保家卫国的道理,他懂。
姐姐说,爸爸极爱干净,早晨她还没起床,便听见扫地声,那是她的爸爸。日子久了,她能从扫地声中听出爸爸身体的好坏。身体好时,扫地声清脆有力,身体欠佳时,扫地声轻轻的、浅浅的……
蹲在房门口,我久久地观察牛怎样吃割剩的禾苗杆。只见它的舌头将禾苗一卷,便进了口中,是没嚼就吞下的那种。它不停地卷吞着,可真能吃。然后,它卧在田里,嘴不停地嚼着,这就是课本上说的“反刍”了。将胃里的食物返回到口中细细咀嚼,再吞下。一群麻雀从它身边掠过,落在田里,叽叽喳喳的,如蜻蜓点水般又齐齐飞起。牛,可没功夫理它们。
门前的绿化带,村委洒下的种子已发芽,开花。䅗䅗的,像个没长高的孩子。或红色、或粉色、或单层或多层的花朵仰望着蔚蓝的天空,不管不顾地在春风中盛开。我惊奇地发现,花丛中竟长出一大片“地菜”。这里从来都不曾见过,它从哪里来?是不是随着花籽一起,离开它熟悉的土地,来到这里落户生根,如同漂泊在外的游子,为了生活离开故乡,在外打拼。当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思乡情切,才发觉,故乡已成了回不去的远方。“日久他乡是故乡”,谁又知道,其中饱含了多少的辛酸和无奈。
平哥家的晚饭过后,有人拉起二胡,笛子随声附和,扬琴敲响,大姐们在乐器的伴奏下唱起了老歌。我㤉异于他们深藏的功底和音乐情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粗糙的手,怎么看都是一个耕种的农民大哥。有的经历坎坷,生活历经磨难。可是,他们依然坚强,依然乐观。
他们年青时都是村文艺宣传队的成员,曾多次代表村里到邻村、县里、市里表演,很受欢迎。直到成家,才渐渐地将重心转入家庭。岁月催生华发,凭着对音乐的热爱,他们再次拿起乐谱,重排当年的剧目。已是爷爷奶奶辈的他们,仍然快乐地歌唱,为曾经的青葱岁月、为坚韧的意志、也为今天美好的生活。
“谁不说俺家乡好”,优美的旋律响起,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感动而又感叹。
有时候,常常会往来时的方向张望,那里有他们的青春,有他们的年少无知,也有上辈的悉心陪伴。
岁月如歌。新居,旧房,都是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