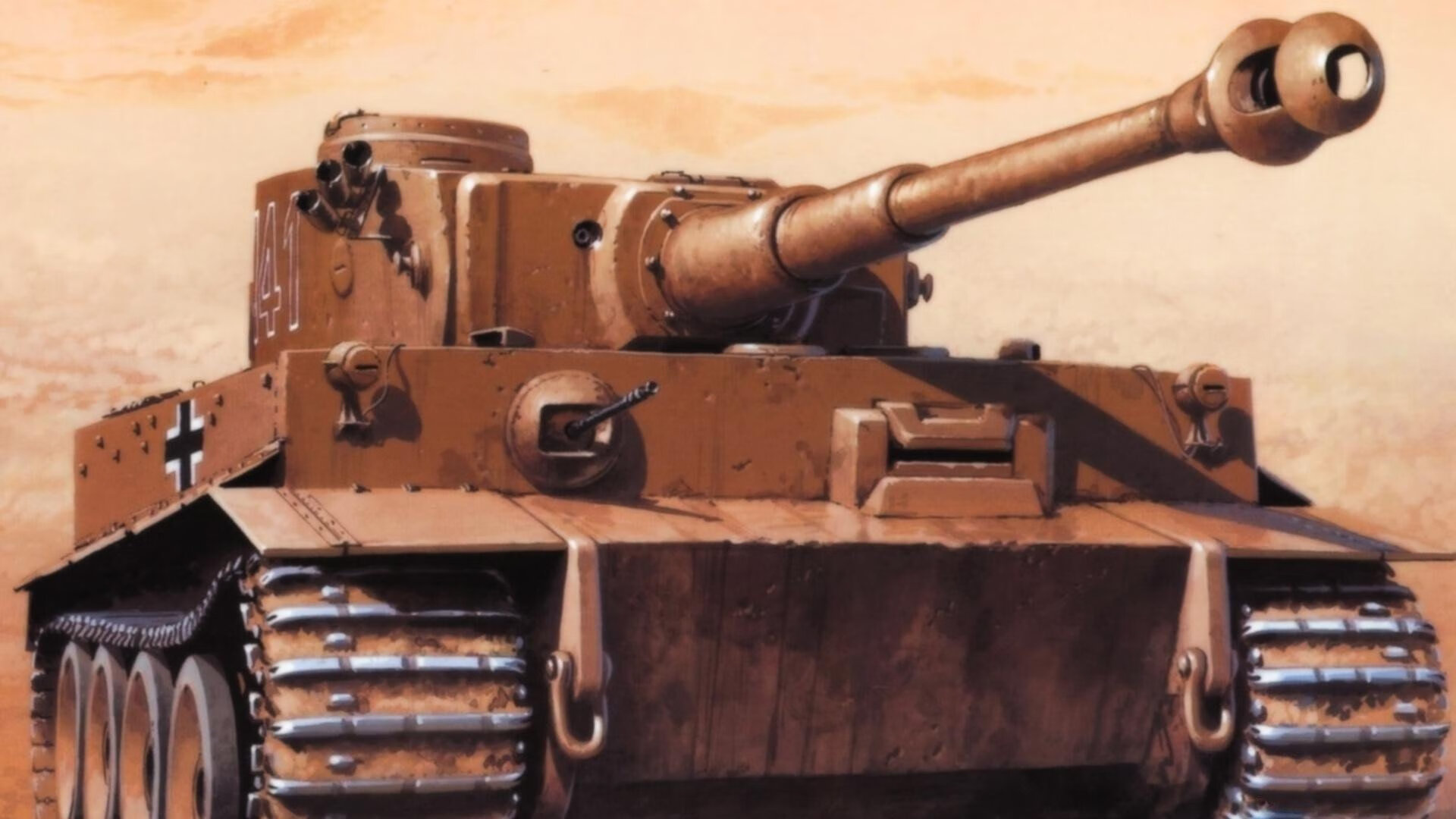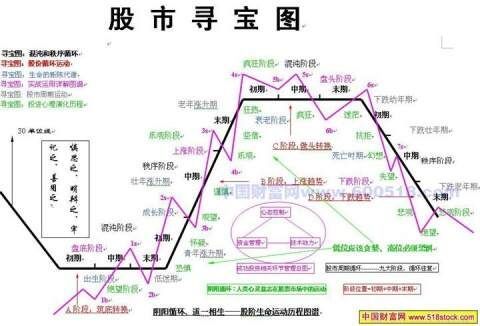杨德昌:冷峻犀利的电影思想家
- 娱乐
- 18小时前
- 288
杨德昌的电影,因为冷峻而朴素的描摹,犀利而悲悯的批判,严肃的追问与自省意识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
台湾新浪潮电影,继承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特性,也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它摆脱了过度刻意的煽情,摆脱了片面的讴歌,专注于用“写实”去解构、批判、反思台湾社会。而杨德昌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更是贯彻发扬了这种批判精神。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继 “都市三部曲”(《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后完成的一次历史批判。
影片借由一场真实的,发生在他身边的少年杀人事件,牵涉出一段禁忌的时代——台湾的60年代,还原压抑的时代氛围与焦虑的个体生存状态,展现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深刻的反思意识。
杨德昌在这部影片中试图触碰台湾的伤口,并以少年的成长经历作为载体,呈现出与之关联的社会图景、众生百态,不回避历史伤痛与时代症结,然而这些症候却如同顽疾一般 在当下的社会中依旧隐隐作痛。这体现了一位艺术工作者的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
2 // 台湾的“病症” //除了台湾人普遍的对身份的迷惘和寻根的渴望,台湾社会的压抑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来源于1949年5月至1987年7月台湾政府实施的“戒严”。
台湾当局为了维护统治权威,对于黑暗混乱的社会局面以及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现实问题采取回避的冷处理态度,掩饰社会的症结,粉饰太平。凡是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凡是展现出左倾倾向的人,都会被“整”,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决。
在五六十年代尤其严重,台湾人人自危。
从八十年代初到解严之前,台湾新浪潮电影虽然是以一种台湾本土化的写实风格在记录和反思,却还是受制于整个压抑管制的社会,就像很多眷村电影一样,多以一种“自传式”的叙述风格来表达一种怀旧、乡愁、对身份的探寻。
而解严之后,虽然台湾新浪潮电影走到末路,但社会批判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禁忌的话题终于“解冻”。人们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其禁锢的自我意识被唤醒。《牯岭街》拍摄于1991年,无疑到了一个巅峰。
01理想和信仰的坍塌和毁灭
杨德昌在电影中为主角小四树立了两位精神偶像——父亲和哈尼。
杨德昌的手记中曾经写道 :“本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
杨德昌为了拍这一段广泛地收集资料,采访,才惊讶地发现六十年代的政治迫害是多么的普遍,而它销声匿迹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都沉默着忍受着,无人愿意主动提起。
小四的父亲被带走,受到政治迫害,经历了一系列的精神折磨。从此父亲就变了。
父亲的变化和逐渐遗失是由社会造就的。父亲遭受到的摧残为小四呈现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逼迫原本“乖巧”的小四的内心更加贴近少年帮派的世界。父亲这一角色是儒家传统观念中中子女的“偶像”,通过对父亲逐步“死亡”的叙述,体现了杨德昌对让伦常身份颠倒的社会的不满。
而哈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这个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投射了杨德昌本人的理想主义,和一定程度上对他所批判的这个时代的某种温情。而这个角色最终还是归于悲剧的毁灭。杨德昌本人给哈尼这个角色配音
正义最终屈服于世间黑暗的规则,情谊被舍去,人们被追名逐利的念头吞噬。哪怕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温情,比如邻里之间的和好,兄弟姊妹间无条件的爱,还是不能避免最终弱小的小四将刀通向另一个弱者。杨德昌用一种十分悲观的态度评价了这个时代。
02社会结构骤变——威权社会日益崩溃, 取而代之的将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兴起。
台湾新电影运动于1986 年宣告结束,而彼时的台湾社会也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伴随着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商业全球化裹挟着新的商业法则、生活习惯、社会文化和价值观进入到台湾社会,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逐渐崩塌,台湾社会和历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全球化语境之中。现代化的都市飞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一系列现代性转型决定了台湾电影的核心焦点也需要进行改变。
当其他台湾新电影在追忆往昔的怀旧中记录思考时,杨德昌大胆解构了台湾新电影群体的怀旧行为。电影悲剧的结局,这种直面惨淡人生的冷酷是其他导演所不忍的。更重要的是,
“当侯孝贤们在后极权时代竭力填补过去岁月的失落和惆怅时, 杨德昌已经预言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台湾社会即使能够摆脱威权统治的压迫, 也会很快陷入另一种资本主义的囚笼。”
一边是个人精神信仰的崩塌,一边是社会结构的转变,杨德昌在这种夹击下,反思着台湾的历史,思考着台湾的现在和未来。台湾应该在文化的夹击中如何自处?人民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守护自我的意识?
3 // 杨德昌的批判性 //电影上映后,杨德昌曾说 :“对我来说,茅武是谁,他为什么杀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大环境。我的出发点是那个时代,可能今天的很多人都宁愿忘掉,但那个时代却对我们这一辈人的人生有过决定性作用。”
“历史和传承” 作为杨德昌作品的共同主线,同时也是台湾新电影不同于其他地区电影新浪潮运动的两大范畴。
对于杨德昌来说,要接近世界的复杂性不仅可以通过故事的多线程叙事结构,更可以跨越多种叙事风格:严肃的、荒诞的、现实的、幻想的,并将这些以一种巧妙的叙述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一一》展示了一个大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看似松散的结构下,正像一张大网把每个家庭成员束缚在其中,每个人不能挣脱。杨德昌用镜头观察着台北。
而台北这个被放大的都市里,如同《麻将》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毫无头绪,只靠着利益驱动而行动的人群,自以为算计了生活,殊不知已经陷入现代都市危机四伏的丛林里。
过度的物质享受腐蚀了现代都市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外表光鲜的驱壳之下包裹的可能是无趣的灵魂。导演杨德昌所关注的人群是广泛的,他们是高度物质化进程中精神状态极度失落的人。
他在电影中选取自己的代言人,向观众传达自己对世界的观察、警示、不安与热情。电影是杨德昌介入社会的方式,是他批判社会、了解世界的手段。同时他又以自己的方法介入电影,甚至清楚地告诉观众,作为设计者的导演本人同样也在戏中。
他是《牯岭街》里的电影导演,犀利直接的言语讽刺着无奈的现实,他是《一一》里手持相机记录真实的洋洋,通过对背影的观察为我们呈现这个“背面”,被我们忽视的,细枝末节的,同时也是揭露现实的背面。
4从影片直观的内容题材来看,大多是侧重于现代城市中的人际关系、都市文化、家庭生活等真实描画,实际上是通过这些看似日常的描述和刻画来揭示台湾社会现代性转化中出现的伦理丧失和价值迷失问题等问题;
杨德昌导演对于台湾都市生活和都市人的深度剖析,对于都市生态的解构能力,对于“个体”和“群体” 的现代性伦理困境的真实、尖锐、生动又细致的刻画,用探索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变迁来筑构主题,使其作品始终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从影片叙事手法上来看,善于利用空间叙事结合多人称叙事,展现着“从一种真实跨入另一种真实”的过程 :即用一种带有记录、纪实性的真实诚恳的表述方式,来向人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靠拢,从而跨入到另一种新的更为深入的真实世界,而这个真实世界是导演所真正要展现的,娓娓道来并不刻意强求。
杨德昌的电影风格受到漫画的影响极大。他坦言:“我想,这不单单和电影有关。我的电影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漫画,美国漫画和绘画的影响。”所以杨德昌是一个用画面讲故事的导演。
参考文献:
1. 康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成长的伤痛.电影文学.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7
2. 何李新.怀旧·爱情·社会 ——论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绵阳师范学院.2010
3. 万传法,田硕.理智与情感: 杨德昌的情感困惑与作者立场 ——杨德昌及其电影研究.上海戏剧学院.2017
4. 孟佳文.论杨德昌的电影叙事及其两大范畴.当代电影.2019
5. 张晔.杨德昌的儒者观 ——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例.上海电影学院
小诺点睛
杨德昌总是被批判为“过于说教”,的确,与侯孝贤极致性的日常化台词和蔡明亮的沉默相比,杨德昌的人物总是显得有些“话多”;在香港,也有话多的导演,他是王家卫;在纽约,也有个话多的导演,他是伍迪·艾伦。从电影类型看上去,他们三个是那样的不同,他们的相同之处却在于他们都是讲述都市故事的大师。熊乾秀这篇文章,正给我们回顾了一遍杨德昌的都市性,这种都市性不仅仅出现在他的故事、人物之中,也寄生于他如同小津安二郎般冷峻的场面调度于长镜头里,也同样,积聚在那些急于表达滔滔不绝的都市人的言语之中。
本文作者
熊乾秀
18级法语
杨德昌导演小组
小组成员 李言,18级英语 朱千驰,19级英语 王天宇,19级希腊语 李洁,18级法语(国际关系) 熊乾秀,18级法语供稿:熊乾秀
排版:熊乾秀
图片来源:网络
你可能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