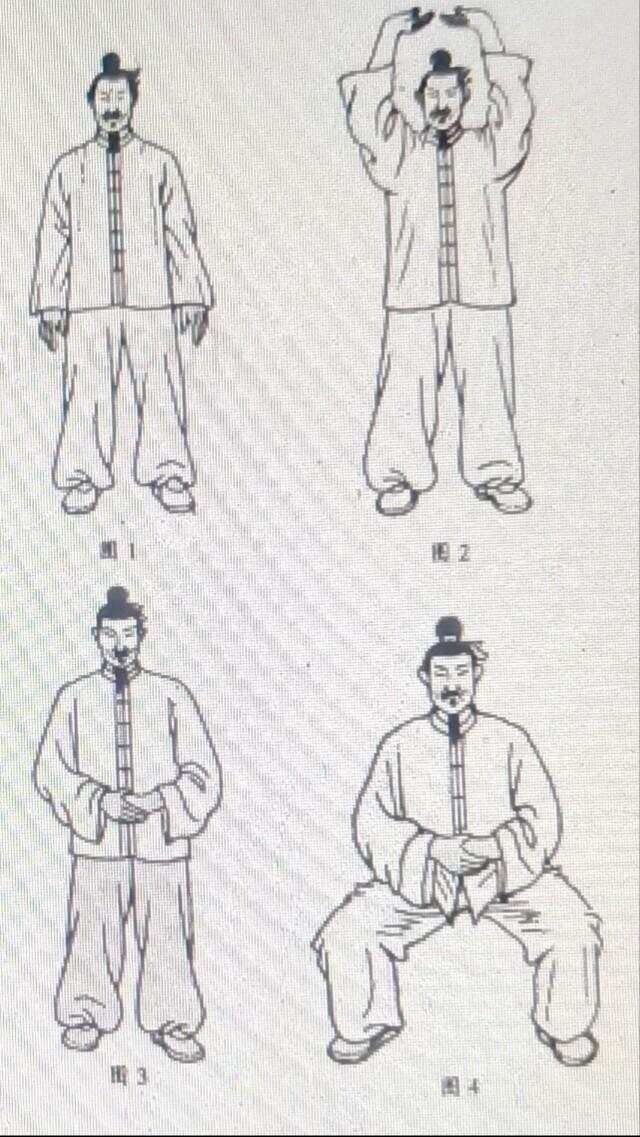这4大类抗风湿药物有治疗新冠感染的作用!你了解吗
- 健康养生
- 4小时前
- 265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放开以来,预防和治疗新冠已经成为当前的重点,而风湿病患者的用药由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典型的免疫系统整体受损,加上皮质类固醇和免疫抑制药物产生的医源性效应,且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感染新冠的风险与普通人群相比要稍高,风湿病药物治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当前的前沿研究中发现,有一些风湿病药物同时具有抗新冠的治疗作用,本文对于当前抗风湿药物作为治疗新冠潜在治疗方案的药物进行了详细汇总总结。
氯喹/羟氯喹氯喹和羟氯喹是广泛使用的抗疟疾药物,具有众所周知的免疫调节特性,已扩展到包括类风湿病在内的几种免疫风湿性疾病。氯喹产生抗病毒作用的能力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为人所知。该药物能够干扰不同病毒(包括SARS冠状病毒)生长和传播的几种机制已在体外研究中得到证实,尽管随后的体内实验存在争议。
在临床可接受的浓度下,氯喹能够增加病毒/细胞融合所需的内体pH值,抑制toll样受体活性,并干扰细胞受体ACE2的终末期糖基化。所有这些功能都可能对病毒受体结合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药物对SARS冠状病毒感染的进入阶段和进入后阶段都有潜在影响。因此,氯喹最近被纳入了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至少10项随机对照试验,在各种方案下与上述抗病毒药物联合治疗COVID-19。来自100多名患者的中期结果表明,氯喹在改善肺部影像学表现、抑制肺炎加重、促进病毒转阴和缩短不同严重程度的疾病病程方面优于对照治疗。最近,在基于药代动力学模型(PBPK)的体外研究中,羟氯喹被证明比氯喹更有效3倍。口服负荷剂量为400 mg,每天两次,然后维持剂量为200 mg,每天两次,持续4天,似乎是治疗SARS-CoV-2感染的最佳选择。
IL-6和IL-1受体抑制剂如前所述,在大多数严重的COVID-19感染病例中发生的ARDS主要是由与病毒复制和肺损伤相关的促炎介质(CRS)的大量释放引起的,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此外,据报道,这些细胞因子的高水平与淋巴细胞的绝对数量呈负相关,存活的T细胞功能衰竭。由于针对病毒感染的有效免疫反应取决于细胞毒性T细胞的激活,CRS可能与病毒清除减少有关,从而导致COVID-19恶化。IL-6和IL-1在这种高炎症性疾病中起着关键作用,这表明它们的阻滞剂可能能够用作SARS-CoV2相关间质性肺炎的治疗方案。来自IL-1阻断剂(Anakinra)在脓毒症中的3期随机对照试验数据显示,过度炎症患者的生存显著改善,并且没有增加不良事件。一项针对21例重症COVID-19患者的回顾性研究表明,托珠单抗可改善大多数患者的CT影像学和氧饱和度,并使CRP水平和淋巴细胞计数正常化。托珠单抗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已在中国获批,目前正在COVID-19肺炎和IL-6水平升高的患者中进行(ChiCTR2000029765),意大利监管药物管理局(AIFA)已批准一项II期研究,将纳入330例肺炎和早期呼吸衰竭患者,主要结果为1个月死亡率降低。此外,生产第二种已上市的IL-6抑制剂sarilumab的公司最近宣布有意进行一项类似设计的研究。
确定COVID-19感染期间CRS的独特定义对于更好地定制重症患者的管理至关重要。在对11例感染COVID-19的中国重症肺炎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中,存在大面积肺损伤(≥50%),CD4和CD8T-淋巴细胞水平下降(低于最低正常范围的50%),外周血IL-6水平升高被认为是发生CRS的最大危险因素。提高铁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沉降率或降低血小板计数可能是鉴别需要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的额外参数。
肿瘤坏死因子(TNF)抑制剂如前所述,SARS-CoV感染与ACE2表达下调以及导致肺损伤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增加有关。此外,病毒刺突蛋白能够诱导TNF-α转化酶(TACE)依赖性的ACE2外膜脱落,这对于病毒渗透到细胞内至关重要。由于这一过程似乎与TNFα的产生严格耦合,因此假设使用TNF抑制剂可以有效减少SARS-CoV2感染和随之而来的器官损伤。
Janus激酶抑制剂如前所述,SARS-CoV-2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进入靶细胞。一些已确定的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调节因子是麻木相关激酶(NAK)家族的成员,如ap2相关蛋白激酶1(AAK1)和周期蛋白G相关激酶(GAK)。抑制AAK1可以阻止病毒进入肺细胞,也可以阻止病毒颗粒在细胞内的组装。在批准用于医疗用途的47种AAK1阻滞剂中,有6种具有高亲和力抑制AAK1。这些药物包括肿瘤药物如厄洛替尼、舒尼替尼、鲁索利替尼和费达替尼,这些药物均已被证明可抑制登革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细胞感染。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化合物只有在显著高于临床实践中通常使用的剂量时才能产生足够的NAK抑制作用,因此对患者具有潜在毒性。
相反,JAK抑制剂巴瑞替尼在经批准的RA治疗剂量(每天2~4mg)获得的血药浓度下能够有效抑制AAK1和GAK。此外,作为JAK 1和JAK 2的选择性抑制剂,巴瑞替尼还能够对COVID-19期间更严重的间质性肺炎的CRS(包括IL-6和干扰素γ)引起的宿主炎症反应产生重要的抑制作用。
最后,巴瑞替尼与相关CYP药物代谢酶的相互作用最小,这使得该药可能被纳入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瑞德西韦等抗病毒药物的联合方案。有趣的是,托法替尼未显示出可检测到的AAK1抑制作用[104],而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批准或测试的其他用于RA的JAK抑制剂(如Upadacitinib或Filgotinib)在冠状病毒感染方面的可能影响。出乎意料的是,目前唯一一项评估网格蛋白介导的胞吞阻断在COVID-19治疗中的潜在作用的临床试验是Ruxolitinib(ChiCTR2000029580)。
另一方面,IFN是在感染早期预防病毒复制的最有效的先天免疫反应之一。干扰素通过JAK/STAT信号通路激活转录,导致几种干扰素刺激基因的上调,这些基因具有快速杀死感染细胞内病毒的能力。几乎所有病毒都通过阻断IFN信号通路来对抗1型和3型IFN的作用,而能够拮抗JAK/STAT通路的病毒编码因子是毒性的关键决定因素[113]。特别是,甲型流感病毒通过降低IFN受体的表达和直接抑制IFN信号通路来破坏JAK/STAT信号通路[114]。因此,baricitinib产生的JAK/STAT阻断肯定会损害ifn介导的抗病毒反应,目前尚未更好地量化其对SARSCoV2感染进展的潜在促进作用。
总之,关于巴瑞替尼可能用于治疗COVID-19感染的证据仍存在很大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阐明其在治疗更严重的病毒性肺炎病例中的潜在作用。
结论新冠流行是一种突发卫生事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复杂疾病的管理。RA作为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其感染风险高于一般人群。合成和生物疾病修饰药物的使用与严重感染发病率的潜在进一步增加有关,但RA疾病活动性控制不良是一个更大的感染风险因素。因此,即使在新冠爆发期间,也应鼓励RA患者继续治疗。
参考文献:
[1]Gracia-Ramos,A.E.,Martin-Nares,E.,&Herná
ndez-Molina,G.(2021).New Onset of Autoimmune Diseases Following COVID-19 Diagnosis.Cells,10(12),3592.
[2]Frommert,Leonie Maria et al.“Type of vaccine and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but not diagnosis critically influence antibody response after COVID-19 vaccination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disease.”RMD open vol.8,2(2022):e002650.
[3]Favalli,Ennio Giulio et al.“COVID-19 infection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Faraway,so close!.”Autoimmunity reviews vol.19,5(2020):102523.
[4]Russell CD, Millar JE, Baillie JK. Clinical evidence does not support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for 2019-nCoV lung injury. Lancet Lond Engl 2020;395:473–485.
[5]焦桐,陈昊,杨静,刘芮妮,张舒恬,吴沅皞.改善病情抗风湿药治疗病毒感染的机制及临床研究进展[J].中国医药,2022,17(03):456-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