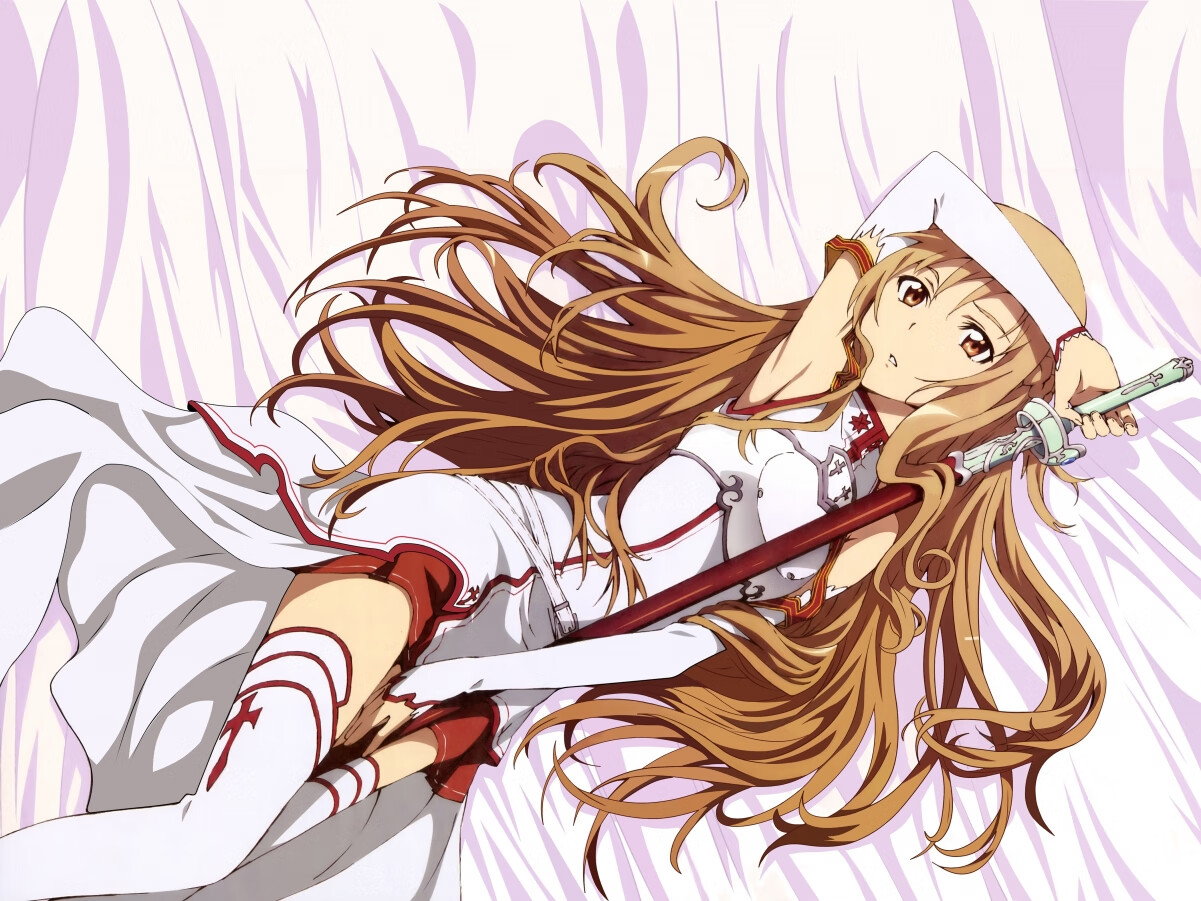《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
- 文化
- 6小时前
- 846

一、问题的由来
《吕氏春秋》一书的结构框架可以用三组数字形式来表示,十二纪:12×5;八览:8×8;六论:6×6,于井井有条之中透露出些许神秘意味。
不少学者指出,《吕氏春秋》全书编排结构及各部份篇数之安排,与古人对于数字的神秘观念有关。杨希枚大约是最早对此进行过认真讨论的现代学者,他的看法是:十二纪六十篇,与六合或六十甲子之类的神秘数字有关,因而,“十二纪可说是据天地之道进而讨论人事是非的一部天书”;“其次,《吕氏春秋》的八览、六论也同样是或象地数,或象天地交泰之数;尤或隐寓六合、六虚、六漠、八极、八表、八伭之类的宇宙观思想。”徐复观、李家骧、洪家义、吕艺、蔡艳等也讨论过《吕氏春秋》数字形式所蕴含的寓意。各家的解释分歧甚大,几乎一人一义。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正是古籍神秘性编撰形式的盛行期,其时著作,“好利用数字的神秘寓意来营建其结构体系”。西汉董仲舒称:“天地阴阳木火金水土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毕数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此也。”《汉书·扬雄传(下)》叙扬雄撰《太玄经》的由来:“(雄)于是辍不复为赋,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这段话表明《太玄经》三卷从首至尾的整个编撰形式都是利用数字的神秘寓意构建的。东汉王充曾批评时人那种“经传篇数皆有所法”的观点,认为“圣人作经,贤人作书”,都是“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王充的驳斥,正好可以证明那种认为书籍的篇目数具有象征意义的观点,是当时的流行看法。
《吕氏春秋》极重视“数”。在《吕氏春秋》中,养生要“尽数”(《尽数》),治国要“任数”(《任数》),国君发布政令要“无逆天数”(《仲秋》),万事万物中都蕴含着“不得不然之数”(《知分》)。《序意》篇提出“无为而行”的理想政治是“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在今存先秦子家著作中,对“数”予以如此高度重视、反复强调的,除《吕氏春秋》外,还有《管子》、《易传》等书。19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也充满了有关数字神秘性的议论。《韩非子》中也有一些这样的议论。这对于我们推寻《吕氏春秋》一书的思想倾向,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吕氏春秋》中,“数”往往可与“术”、“道”等词通用,但《吕氏春秋》中的“数”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所说的“数”,往往可以与具体的数字和具体的事物对应。如《季冬》:“数将几终,岁将更始”,此“数”指十二月之数;《本味》所称“四时之数”,说的是具体的“四时”轮替。综上所言,可见《吕氏春秋》对其时有关“数”的神秘化观念非常熟悉,并且富有兴趣。
植根于这一文化氛围之中,本身又对“数”的神秘意味有着浓厚兴趣的《吕氏春秋》,选用这样一组数字来构建其理论大厦,便不会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无甚深意,仅仅是些无关痛痒的小小智力游戏,而是有着明确的用意,即用这些数字来寄托其理念,体现其撰述意图。不过,象12、5、8、6这类数字,在古代都具有多重神秘寓意,要确指《吕氏春秋》所采用的究竟是这些数字的何种寓意,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显然并不容易。这也正是学界在此问题上异说纷呈、意见难以统一的原因所在。此处谨在前贤时哲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吕氏春秋》成书时代人们对数字神秘性的附会,结合《吕氏春秋》本身的相关论述,对此问题试作解答。
二.12×5之寓意
“12”这个数字,在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里喻指天道的运行。一年之内,月亮的盈亏圆缺重复十二次;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即从地球上看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天,历时十二个月;岁星在黄道上绕行一周天,约为十二年。至迟从《夏小正》开始的,以阴阳合历为特征的古代中国历法,便非常注意对这几种天象的观测,因而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12”具有天道运行之规律的意味,是“天之大数”。《左传》哀公七年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后汉书·荀爽传》言:“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可见此种观念之根深蒂固。《吕氏春秋》十二纪按十二月顺序,将各种人事分类编排于其下,而其内容又贯通了对终极的、普遍的天道的追寻,它对“12”这一数字的运用,正表现了“12”作为具体的“十二个月”和抽象的天道象征这双重涵义。
“12 ”既是“天之大数”,天人类推,便也可以用来表示人道的极致。上引《左传》及《后汉书》文表明,在古人眼里,“天之数”即是“天子之数”。徐旭生认为“以十二为大数,始于周人”。此说难以确考。不过在周代典制里,“12”是天子之数,是制礼用物的上限:天子之冕,十有二旒;天子礼服,十有二章;天子之旗,十有二旒……其余等级依次逐级递减。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中,“天之数”与“天子之数”交融在一起,天子的衣食住行与天象的盈虚消长息息相应,共同规定与体现着世界的理想秩序。纪首之外四十八篇,论题及于“人道”的方方面面,而处处显露着欲究明天人之际的意图,专注于普遍性“道”、“理”的探索。其只从正面阐述的行文风格,和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都在刻意营造一种法典般的权威性和感染力,表现了欲为新天子创制立政的强烈意图。
十二纪每纪五篇,按李家骧的意见是喻指五行:“每纪首篇辖四篇指四方,加首篇为五,合五行之数。”吕艺、洪家义则认为此五篇之数,符合《易传》中的“天之中数”。从“5”这个神秘数字的起源看,它既是指“天地之中数”,同进又隐含着“五行”之意。“5”作为神秘数字之出现,乃是四方划分的空间意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最初是指位于四方之间的“天下之中”,五方取代四方的过程是在殷商时代开始的。而随着东西南北中五方观念的定型,“5”这个数字逐渐被看成是宇宙万物的共通的、普遍的结构和秩序,此即“五行”观念之滥觞。
在《吕氏春秋》十二纪里,“12”与“5”的搭配不只表现在篇目数字的设定上,也渗透在文章内容之中。“12”这个“天数”不仅具体表现为一年十二个月太阳的运行,更表现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样一个天道周期。而十二纪纪首在四时流转的秩序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五行轮替的秩序。郭沫若当年曾根据十二纪纪首及《管子·幼官》所记,列了一张五行系统配合表。今根据十二纪中已成系统的说法,对此表略作修改,以见十二纪中的五行系统,及其与天道——四时的配合:
从这个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四时与五行的配合,四时序时、五行类物,这样一个井井有条的大系统似乎可以包罗万象。不过从这个表里亦可以看出四时与五行相配的牵强性:因为一年只有四时,中央土(黄帝)在四时的序列中是虚位,只能附于季夏之后。郭沫若认为十二纪纪首“已经采用着石申(战国时魏人)二十八宿的完整系统,而渗透着五行相生的配合”,“这论理不是吕氏门下所撰录,但不能出于战国以前”。徐复观则认为《吕氏春秋·十二纪》,是在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之上,“直承其发展而加以组织化,具体化的”。而无论十二纪纪首是否出自吕氏门客之手,要之其体现了邹衍学说的精粹,则是无庸置疑的。因而,十二纪每纪五篇这一数字之设立,应当主要是从“五行”这一意义上考虑的。象征天道运行规律的“12”,与象征天地万物有序化的五行之“5”配合,显然具有穷究宇宙奥秘、规范万物秩序的意味。
在战国秦汉期间,“12”与“5”似已逐渐成为固定组合,是天子之制的象征,同时似乎还是天地呈现其奥秘,人从而把握天地之奥秘的神秘途径。《礼记·礼运》有一段话,讨论了“12”与“5”组合的巨大、神秘的作用:“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此种观念不知起于何时,但应该是在阴阳五行学说流行开来的战国中期以后。西汉时期,此观念似已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并已纳入国家典制。《汉书·郊祀志》记武帝时,“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犊黄焉”。在汉代被炒得纷纷扬扬的明堂之制,就《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汉书·郊祀志》等材料的记载或描述来看,其实就是体现了“12”与“5”组合的一座建筑物,其神秘性、象征意义正赖于此。
“12”与“5”的组合在《吕氏春秋》编成的时代,或许尚未能产生如西汉时期那样大的震撼力,不过西汉时人赋予这一组合的象征意义,在《吕氏春秋》的时代应已经出现,在《吕氏春秋》书中也有所体现,由此看来,《吕氏春秋·十二纪》采用“12×5”这一数字形式,实欲表明其所论是蕴含着天地之奥秘,体现了“道”之根本的天子之制。
三、8×8之寓意
八览结构可用“8×8”来表示。对于这一数字形式之寓意,有关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认为八览之八,喻指八方。如徐复观称“八览云者,乃极八方之观览”;杨希枚认为八览“象地数”,隐寓“八极、八表、八伭之类的宇宙观思想”。其二、认为八览取法八卦之数。洪家义、吕艺、蔡艳等持此见。吕艺进而称:“‘八’这个数字自八卦始创之日,就与人事关连”,“八览以八与八组合而‘中审之人’”。
八览总篇数共八八六十四(今佚一篇),与《周易》六十四卦之数合。《易》筮盛行于两周,西周彝器上或刻有表示筮占结果的数字组合,《左传》中有不少用《易》占卜的故事和对占筮结果的解说,即是明证。孔子之后,《易》为儒家六艺之一,研习转精,而《易》作为宗周旧籍,在非儒家的战国学者那里,也是很受重视的。吕不韦及其门下宾客,对《易》及其数字系统应该很熟悉。《吕氏春秋》中有三处直接引用《易》经经文,因而他们在确定八览八八六十四这一数字形式时,不会想不到《易》的八八六十四卦,或许也有一点与之比附的意图。八卦相重,可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八览篇数结构如此安排,大约也有极物之变化的用意。
不过,在古代中国,神秘数字“8”更普遍、根本的寓意,是隐指向四面八方展延之“地”。《管子·五行》称“地理以八制”。在《易》传中,“8”为地之极数。古人在谈论地之极广极远以至杳冥不可考的远方时,率用“八ⅹ”这一固定格式。如《淮南子·坠形训》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八纮之外,乃有八极”。其他如“八荒”、“八冥”、“八漠”、“八虚”等词,都表现了八与地的关系。“8”为地数这一象征意义,浑涵包容,其他与“8”有关的象征、习语,都是植根于这一根本观念之上或受到此观念的渗透、影响。吕艺文中引用过的《汉书·律历志》中一段文字,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
“8”喻指“地”,在古人的观念里,天道圜,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故本为“地”之象征的“8”,又引申出了臣道、治术之寓意。《尚书·洪范》称治理国家有“八政”。而在《周礼》中,“8”寓指具体的治术这一点尤为突出: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吕氏春秋·八览》纵论统治之术而以“八”为序,其内容与《周礼·太宰》之“八法”、“八则”、“八柄”、“八统”颇可相通,两相对照,似能说明八览偏重臣道、推究治术之用意。《管子·幼官》有一句话,“八分有职,卿相之守也”,正可为八览之注脚。
本文前面在讨论八览的内容与结构时已经指出,八览首篇《有始》有总摄八览,甚至统贯全书之意义。《有始》文中遍说九野、九州、九山、九塞、九薮、九风、六川等地象,看似难以理解,但若从“8”为地数,八览表地这个角度来看,就豁然开通了,《有始》遍说地象,正体现着八览极八方之观览,隐寓治术万端之命意。
四、6×6之寓意
“12”与“8”两个数字,虽引申出多重象征,但在战国之世都有一个基本的内核,一象天道,一为地数,数字“5”涵义稍杂,但在战国后期主要喻指五行,其寓意也相对明确。比较起来,在战国秦汉之时,数字“6”蕴义最为复杂。
“6”的神秘性大约有两个来源:
其一,“6”最根本的寓意当是用来表示天地四方,即六合。这应是随着古代中国人宇宙空间意识的成形而出现的。《荀子·儒效》曰:“宇中六指谓之极”。《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在战国时期,学者常利用“6”的这一寓意构造新词,以便能更形象地传达出宇宙空间广大峻深无涯无际之意。如《庄子·应帝王》称天地四方为“六极”:“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楚辞·远游》则称之为“六漠”:“经营四方兮,周流六漠”。
其二、六爻。《易》一卦六爻,六爻按排列顺序分别象征天地人的说法不知起于何时,但肯定是在“6”象“六合”这一意识熏染之下出现的。在战国时期,这种说法无疑已经成为普遍的观念。《易·系辞下》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易》之彖、象释卦象、占吉凶,极重视爻位的变化。
在战国秦汉之际人们的观念世界里,“6”同时还是固定的统治秩序之象征,与“人道”密切相连。《管子·五行》称“人道以六制”。《新书》中有一篇《六术》,极言人之活动与“6”的神奇关系:“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兴,乐兴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依“6”为制,似乎成了调理人道秩序的方便法门。“6”的这一寓意在古代中国的影响,并不比“六合”“六爻”稍逊。中央行政机构依六设置,在古代中国成了一种定数和传统,如周之六卿、唐以后之六部、唐地方衙门之“六曹”、宋地方衙门之“六案”。
“人道六制”观念不知起于何时。上文谈到“6”的神秘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寓指天地四方六方位的六合,一是兼三才而两之的六爻。无论是哪个来源,都隐含着“6”有贯通天地人的神秘特性,这大概就为“人道六制”的观念打下了基础。我们看到,无论是《周礼》中的六卿,还是后代的六部尚书,其执掌多与天地四方附会,而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名目(四时与四方很早便已确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因而,“人道六制”之出现,恐怕与古代中国的天君同道观念密不可分,它体现出早期统治者将自己打扮为宇宙王的意图。虽然后来社会复杂化,政事渐繁,用这种简单的模拟已不足以应付政事,但帝王为六合之主,设官有天地四方之制的观念一直沿袭了下来。尽管后世所称的六官,其职掌与天地四方的关系,仅剩下一些经验性的比附,但这种超稳定的职官结构,显示了早期传统的牢固性。
《吕氏春秋·六论》采用“6×6”形式之寓意,大约正是利用了数字“6”的多重寓意,既象六合,又寓“人道六制”之意。六论内容广泛,而篇首《开春》首先泛言物之相应,显然有究极六合之理的意味。再就六论立论的角度来看,较之十二纪、八览,显然偏重于人(士)的视角。首篇《开春》统贯六论,而举善说之事,与《序意》篇所言“人曰信,信唯听”之意若合符节;六论以《士容论》作结,其侧重人(士)的角度更彰显无遗。整个六论的编排次第与各论之要点,似能符合上引《新书·六术》所说的“德”之“六理”:《开春论》言“道”;《慎行论》论士之“行”,“行”即“德”;《贵直论》涉及到士之“性”,因为《吕氏春秋》是将“直”视为士之“性”;《不苟论》中如《博志》篇,谈到如何做到“神”;《似顺论》辨析是非物理,自然切合“明”义;《士容论》所论,可以视为士之“命”,即士之命定、本份。因为《新书·六术》并未说明“德”之“六理”各有何具体表现,此处所言,仅属推测,不敢说六论的编排必有此意。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六论对“人”的讨论,是主要以“士”为对象,论“人”即是论“士”。
一些学者认为六论在《吕氏春秋》三大组成部分中代表着“下验之地”的方面,其根据有二:一是《汉书·律历志》称“6”为“地之中数”,一是六论末四篇谈农业,寓指“地”。如洪家义称:“六论每论六篇,是符合地之中数的”,“六论以《上农》四篇殿后,明显是与地利相应的”。吕艺认为六论是法地,关键在于最末四篇农学文字,因为农与地相关。他摘取《汉书·律历志》语,力言“6”可配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汉书·律历志》中的数字系统,是两汉时人用乐律之数和《易》传之数对各种数量关系进行整合的结果,它对数字神秘性的理解,与战国秦汉之际人的想法已有了很大距离,单凭《汉书·律历志》的说法,不足以说明《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这一点尤应引起论者注意。本文稍后还将讨论这个问题。至于以为《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谈农业而寓“地”之意,其说更不足为据。黄伟龙便指出:“至于六论皆为地之说,尤为难信,洪家义所谓‘地者底也’,故把《上农》四篇放在《吕氏春秋》之末,实《上农》诸篇为农业知识而非地理知识,《吕氏春秋》中地理知识,主要在《有始》一篇,何以不把《有始》放在六论?”黄说甚是。较之农与地,农与人的关系更密切。农是民的职业、身份,《吕氏春秋》中的“民”,显然是指农民,十二纪纪首中的“民事”,都指农事,而《上农》一篇极力陈说务民于农可利国化俗,已点明了编入此四篇的意图,而这应该正是《吕氏春秋》的编者将此四篇连同《士容》、《务大》两篇统一称为《士容论》的原因。六论喻人,这一点殆无可疑。
五、如何理解《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
在战国中后期,有许多学者将探索天地万物所具有的特定数字表现形式,当作探索宇宙、人生、政治的根本途径或方法来看待。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著作,如《管子》、《黄帝四经》、《韩非子》、《吕氏春秋》,包括《荀子》中,“数”的涵义与“道”相当接近,并往往可与“术”字通用。这种新的思想兴趣(或可称为知识兴趣)之兴起,可以视作思想界逐渐摆脱了西周晚期以来对天命鬼神等既有秩序的怀疑情绪,而试图利用各种关于天地人的知识(包括迷信)重新把握宇宙秩序之努力。对于其时思想界的这种新动向,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由于受《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等对诸子学说的界说影响,一般倾向于将其视作某一家一派——比如阴阳家——的个别主张。研究者在解释《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时,也往往本着此认识,而致力于发现数字背后的学派倾向。一些研究者虽然并不认为《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有提出来进行专门探讨之必要,但他们实际上有自己的看法,而他们对《吕氏春秋》总体思想倾向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看法左右。如陈奇猷认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是阴阳家之学,他的理由是:“阴阳家的学说是全书的重点,这从书中阴阳说所据的地位与篇章的多寡可以证明。在位置上,阴阳说安排在首位,数量上则阴阳说占有最多的篇章。”而陈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对“天数”的推求是阴阳家说的重要方面,故把《吕氏春秋》中凡有这方面说法的篇章都看作阴阳家说。熊铁基提出应把《吕氏春秋》看作是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他认为新道家比起先秦道家来,更系统、更理论化,而其原因在于“新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熊氏眼中的“因阴阳之大顺”,正是指盛行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对宇宙万物特性、规律的数字化理解,即《淮南子·泰族训》所说的“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之类。此外,金春峰认为《吕氏春秋》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而不是道家的“天人对立”的思想,是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不是道家的反人文主义的思想,这一认识也显然蕴含着对《吕氏春秋》贯通天地人的数字形式的理解。
由于思想来源和兴趣点的稍许差异,战国后期思想界对宇宙万物的数字化秩序的探索确实表现出了家法、学派的区别。这种家法、学派的区别,无疑有着地方文化的背景,而它们在总体倾向、思考路数等方面的令人惊讶的一致性,则提示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共同传统和基本倾向的存在。当时思想家们津津乐道的,认为体现了宇宙之秩序的“数”,大致可分为这样三类:
一、历数,即与历法有关的数,如四时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天等,这被认为体现了天道运行之规律。汉代司马谈一则称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一则称道家“因阴阳之大顺” ,可见试图用“历数”规范人事,是这两派思想家的特点。儒者荀子在《天论》里极力批驳治乱吉凶上应于天“数”的说法,恰能说明此种观念在战国后期非常流行。荀子本人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但他的主张乃是一种超迈于时代的高标特出之见,对其同时代人,甚至之后数百年间的影响都是很小的。我们从《易传》、《尚书·尧典》、包括《孟子》、《中庸》等书里能体会到的是战国儒者对“天之历数”的痴迷追寻。
二、律数,即乐律之数,主要指黄钟等十二音的律管寸数。《周礼·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周礼·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音律之被神圣化,大约与古老的风角占卜之术有关。而黄帝命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定律管之制的传说,则暗示了乐律之数被神圣化的东方背景。律数之流行与邹衍及燕齐方士当有莫大干系。
三、《易》筮之数。六爻成象,八卦通情,六十四卦极人事之变化,这些观念在战国以前应已流行。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则在新的知识基础之上对这些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易·系辞》的“大衍之数”,以数之奇偶喻指天地阴阳,将数列的奥秘与宇宙的奥秘等同起来。对“数”的这种新的理解和运用,应当主要是儒者的贡献,道家的影响可能也有一些。
战国之世最受重视的神秘数字,首推历数。阴阳家言“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黄老道家的“四时刑德”之说,都是致力用“天数”来指导人事。孟子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是基于天象历数而得出的认识。
历数为天之数,律数为物之数(律管之数)。律数最初似并无多少神秘意义,它同度、量、衡等一样,只被视为“数”的运用,而非“数”的神秘性的根源。《尚书·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孔子述古帝王之政,称“谨权量,审法度”,都是就事论事,看不出有什么神秘意味,而且所言都不及“历”。律历合言,应在战国。《吕氏春秋·音律》及十二纪纪首已将律历混同,但是是以历统律。汉兴,张苍首律历事,《史记》八书中有《律书》、《历书》,先律后历,显示其时人心目中,律数的神圣性已渐超过历数。至《汉书·律历志》,则认为“数者”,“本起于黄钟之数”,在律、历、度、量、衡等数量体系的排列中,律数居于首位,余者被认是由律数所引出,而擅长历算计数的人在两汉之际被称为“通知钟律者”。这大约是因为传说中将律数的制作归功于黄帝,而战国秦汉正是黄帝崇拜不断强化并最后确立至尊无上地位的时期,故律数在神秘数字体系中也逐渐拥有了至上的权威。
《易》筮之数虽起源甚早,在很长时间里似乎只是单纯利用并附会数字的现成寓意。《易》数之自成一独立系统,应与《易》传对“数”的阐发分不开。在战国时期,《易》传之数似属于小范围内的高深知识,到了两汉,对《易》传之数的庸俗化理解才在民间流行开来。
《汉书·律历志》将律数、历数、《易》数合而为一,在“数”的意义上把它们统一起来了。这与《吕氏春秋》时代的认识有所不同。故用《汉书·律历志》的说法来证成《吕氏春秋》是错误的。
虽然如此,若稍加分析,便可发现战国后期不同取径的思想家们所运用的神秘数字其实基本一致,主要就是10以内的十个自然数,以及“12”、“36”、“72”、“81”、“360”等数。而且,不同思想家们对上述数字寓意的解说虽然并不一致,却反映出每个神秘数字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意义内核,思想家们的解说并未脱离这个内核,而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其进行引申、说明或借用。因此,战国后期思想界对“数”的理解,应植根于一个共同的传统,有着共同的思想背景。这就是弥漫于上古至秦汉观念世界里的数字崇拜。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里,有着浓厚的将世界数字化、数字神秘化的倾向。这种现象之发生,是古人将现象世界反复归类的结果,他们把“相似与相近的归为类,序为数,这类与数,一经一纬,便成了初民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在早期民族中大多存在着将数字神秘化的思维习惯,而这可视为初民试图将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抽象化、秩序化的最初尝试。在古代中国,关于数字的神秘化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我们在卜辞、金文中,在《尚书》等早期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观念的印迹。而这种观念在后来更被体系化、绝对化,成为一定时期内人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葛兆光写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中国古人对世界及其秩序的数字化理解,并将其视作上古至秦汉思想史的一般背景。葛氏的讨论揭开了向来为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所忽视的古代中国思想的底色之一,不过这一底色与不同时代、不同知识基础渗透吸纳而呈现出来的差别与变化,葛氏则甚少留意。对于细化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战国秦汉思想史研究而言,有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差别与变化,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如前所述,战国后期思想家们对神秘数字的理解和运用已经体系化,并已出现了混同化的趋势,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学派的区别。一些《吕氏春秋》的研究者试图发现此书数字形式背后的学派倾向,是有道理的。
不过,对《吕氏春秋》各部分寓意之探讨,却表明很难用某一家一派来圈定这一形式。《吕氏春秋》对数字神秘性的理解和运用,无疑具有强烈的阴阳家色彩。十二纪“12×5”的数字形式,以及纪首排列的五行系统,都显然出自阴阳家的影响。但是否可以说它的整个数字形式都是阴阳家的呢?恐怕很难。邹衍等早期阴阳家的一些主张,如四时与五行的结合,“无逆天数、必顺其时”等,到战国后期已成为流行思潮,是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们乐于探讨的问题,故不能简单视之为阴阳家的一家之说。至于八览“8×8”、六论“6×6”的寓意,有《易》筮之数的影响,但主要是基于很早便已形成的这些数字的“意义内核”,是其时人的普遍认识,并非某家某派的个别学说。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的神秘数字体系,是以历数为主,兼用《易》筮之数,来统合已成常识的神秘数字。较之其时一些思想家的高蹈凌虚之论,它更多地表现出了从古老的传统和普遍的常识中寻求智慧,破解天、地、人奥秘的意图。这说明它无意参与思想界内部的争论,而希望将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比个别学派观点更普遍更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吕氏春秋》因此营建了一个容纳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和百家异说的宏大框架,能够左右逢源,取众之长。
对于战国秦汉时人来说,《吕氏春秋》数字形式之寓意,应当是一目了然的。这应该就是《吕氏春秋》一书的结构在其时大受欢迎的原因。推崇《吕氏春秋》结构的人,如司马迁、刘勰等,其本人也沉迷于神秘的数字编撰形式。《吕氏春秋》的数字形式之发生疑问,大约是唐以后事,这其间有思想进步的成分在,但更为根本的,应是社会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古今文化膈膜而带来的生疏感。(庞慧)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 群聊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