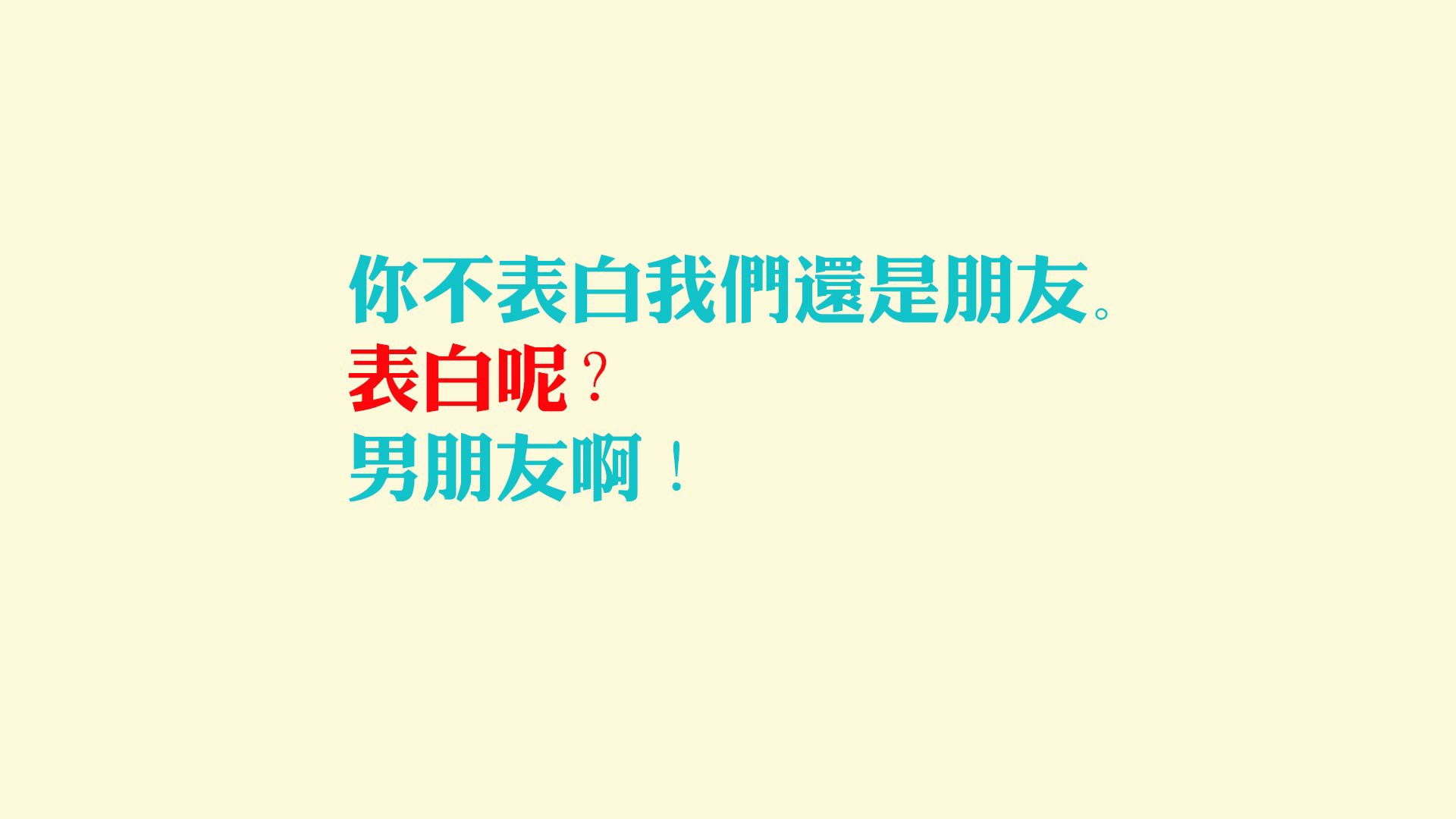闲话《金瓶梅》一百四十七:爱月伺庆,四嫂战情(下)
- 文化
- 2天前
- 201
西门庆见郑爱月将“三泉诗舫”用笔抹去了“三“字,自然又产生了一种征服他人的快感,满心欢喜,两人将话题转移到林太太身上。西门庆向郑爱月炫耀,自己如何征服了林太太,并且将林太太的儿子收为义子,郑爱月拍手笑道:“还亏我指与爹这条路儿,到明日,连三官儿娘子不怕不属了爹。”对于郑爱月的此番表现,有批评者用言简意赅的一个字作了点评:恶。郑爱月为了报复自己与王三官的私人感情纠葛,借西门庆之手让王三官和李桂姐受了一番教训,带入了无辜的旁人林太太,不惜伤害这位未曾谋面、蒙在鼓里的可怜女子,甚至还颠覆了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虽然上这在客观上满足了林太太的需求,但是这招假途灭虢可比得上王婆的借刀杀人了。郑爱月年纪小小,却心机歹毒,毫无下限。只到林太太并不是郑爱月计策的全部,她的终极目标是王三官那个从未出现过的老婆。西门庆说:“我明日先烧林太太一炷香,到正月里,请林太太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灯吃酒,看他去不去。”郑爱月道:“你还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样标致,就是个灯人儿也没他那一段风流妖艳。今年十九岁儿,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儿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儿,不愁不是你的人。”所幸当林太太赴约上西门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带上自己的小媳妇,因为“小儿不在,家中没人”,不知到底是西门庆道高一尺还是林太太魔高一丈,如此简单而又家常的理由,轻易就打破了西门庆精心安排的计划。当然了,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没了一睹王三官老婆芳容的机会。郑爱月一番话,勾动西门庆的天雷地火,热情似火,两个便开始欢娱,此处摘录被删减原文:
两个说话之间,相挨相凑。只见丫鬟又拿上许多细果碟儿来,粉头亲手奉与西门庆下酒。又用舌头噙凤香蜜饼送入他口中,又用纤手解开西门庆裤带,露出那话来,教他弄。那话狰狞跳脑,紫强光鲜,西门庆令他品之。这粉头真个低垂粉项,轻启朱唇,半吞半吐,或进或出,呜咂有声,品弄了一回。灵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欢。粉头便往后边去了。西门庆出房更衣,见雪越下得甚紧。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打发脱靴解带,先上牙床。粉头澡牝回来,掩上双扉,共入鸳帐。
两人玩到一更方罢,起来整衣理髩,重整佳肴,二人又饮勾几杯,西门庆方才作别。骑马打伞,一路踏雪到家。接着作者笔锋又转向另一个女子,贲四的娘子。平时贲四在家的时候,西门府上的玳安等人就经常在贲四家喝酒,现在贲四随夏家上了东京,玳安等人上贲四家喝酒的频次更多了。而西门庆对四嫂早就留意上了,于是叫来玳安,要他去和四嫂暗示一下,如果她肯的话,那就留下一条汗巾作为信物。很快,玳安就带来了四嫂的汗巾。很明显,四嫂并没有拒绝西门庆的暗示和邀请,而她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拒绝西门庆。到了晚上,西门庆迅速撞入四嫂的房间,四嫂也从门中迎接西门庆,两个人之间除了四嫂一句怕人看见之外没有一句客套话,脱衣解带就把事情办了,此处摘录被删减原文:
这西门庆见没人,两天步就走入贲四家来。只见卉四娘子儿在门首独自站立已久,见对门关的门响,西门庆从黑影中走至跟前。这妇人连忙把封门一开,西门庆钻入里面。妇人还扯上封门,说道:“爹请里边纸门内坐罢。”原来里间槅扇厢着后半间,纸门内又有个小炕儿,笼着旺旺的火。桌上点着灯,两边护炕糊的雪白。妇人勒着翠蓝销金箍儿,上穿紫绸袄,青绡丝披袄,玉色绡裙子,向前与西门庆道了万福,连忙递了一盏茶与西门庆吃,因悄悄说:“只怕隔壁韩嫂儿知道。”西门庆道:“不妨事。黑影子里他那里晓的。”于是不由分说,把妇人搂到怀中就亲嘴。拉过枕头来,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来就耸。那话上已束着托子,刚插入牝中,就拽了几拽,妇人下边淫水直流,把一条蓝布裤子都湿了。西门庆拽出那话来,向顺袋内取出包儿颤声娇来,蘸了些在龟头上,攮进去,方才涩住淫津,肆行抽拽。妇人双手扳着西门庆肩膊,两厢迎凑,在下扬声颤语,呻吟不绝。这西门庆乘着酒兴,架起两腿在胳膊上,只顾没棱露脑,锐进长驱,肆行扇蹦,何止二三百度。须臾,弄的妇人云髻蓬松,舌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门庆则气喘吁吁,灵龟畅美,一泄如注。良久,拽出那话来,淫水随出,用帕搽之
结束后,西门庆为四嫂留下了五六两银子和两对头簪。这是全书唯一一处如此直接,如此高效率,如此开门见山,没有客套话,没有前戏的描写。尽管西门庆进入的是一个“浪水热热”的身体,但作者所描绘的却给我们一种冰冷的空洞和即将逝去的虚无。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到这个时候,西门庆做这种事,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快感,而仅仅是为做而做,条件反射一般,倒像是在通过这种疯狂的举动挽回即将烟消云散的存在感。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贲四嫂带水战情郎
在此之后,西门庆通过玳安为中介,多次与四嫂相会,如此朝来暮往,自以为天衣无缝无人知晓,却被韩嫂看见,传到后边潘金莲知道了。而奇怪的是,潘金莲并没有声张开来,也没有找西门庆算账。这种有悖常理的描写,张竹坡用了一个字“冷”来评,似乎很有阴森诡秘的气氛。腊月过半,新年将至,往南方买货的韩道国、来保、崔本等人将要回来了,崔本先回,为西门庆带来一个消息:苗青物色了一个扬州千户家女孩子,只十六岁,“说不尽生的花如脸,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袜如钩,两只脚儿,恰刚三寸。端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名叫楚云的美女子来伏侍西门庆,并替他打妆奁,治衣服,随后由韩伙计船带来。西门庆听后满心欢喜,可能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把她纳为自己第五个妾。对此读者可能也是高兴的,因为新人物的出现意味着新故事的开始。可事实上,再过两回书,西门庆就不在了。如果说王三官的老婆是西门庆相见见不到的第一个女人,那么楚云就是第二个了,直到死,西门庆都见不到楚云。其实在西门庆即将丧命的前几回,也就是在潘吴大战之后的几回,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反复描写西门庆不断高涨的性欲,包括郑爱月、贲四嫂,郑爱月口中的王三官娘子,崔本口中的楚云,下一回的林太太和如意,描写频率如此反常与密集,似乎都在为最后潘金莲强行与西门庆行事后西门庆命丧黄泉而耗尽西门庆仅存的血。此处的楚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千户之女”。我们知道,西门庆本身就是五品提刑官也属于千户,大老婆吴月娘也是千户之女,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楚云大概是一种暗示:出身千户的楚云,在家道中落之后也会沦落到卖身的境地,而身为千户和西门庆以及千户之家的西门府,在西门庆倒下之后,也终将逃避不了猢狲散,家产尽的宿命。对此,张竹坡也评:“即用千户女,可伤西门之心”。但是对于西门庆,对于读者,谁又会相信相同的命运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又有几个人会从别人的命运中反思自己的命运呢?个体的失败并不能阻止群体的前进,同样的,个别的死亡并不能阻止群体继续活下去。别人的故事、小说,在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大家口耳相传,茶余饭后的故事罢了。正是:劝君不费镌研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上一篇
一种治疗中风偏瘫的胶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