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之祸:比靖康之耻还耻辱,10万士族成俘虏,举家北迁有多惨
- 综合
- 9小时前
- 158
自南朝梁末侯景之乱,建康失陷,西魏破江陵,梁元帝被杀,下至陈霸先建陈前后与北齐军队及梁将王琳的争夺,长江流域叠经战祸,民众播离,“斯文尽丧”,堪称六朝时代前所未有之乱局。

值得注意的是,其间南人大量流入北方,与永嘉之乱以来北方人民成批南迁,形成对比。
1、侯景之乱南人之北迁
侯景乱梁,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建康城内外“横尸满路”,“不暇埋瘗”,其悲惨之状见诸史书。
《陈书》卷二一《萧允传》称,“时寇贼纵横…衣冠士族,四出奔散”,“侯景攻陷台城,百僚奔散”。
“衣冠士族”虽说是“四处奔散”,实际上主要是逃往荆州,《萧允传》附弟萧引传:“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
东晋南朝自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当时都督上流的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实力最强,台城失陷后受命承制,故被流亡的朝士视为平定侯景、复兴梁室的希望所在。
侯景之乱中北入北朝之北齐的士人不算多。
最早的是太清元年(547)率军攻伐东魏以接应侯景的贞阳侯萧渊明,寒山之役大败后,东魏“尽俘其众”,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北兖州刺史胡贵孙、谯州刺史赵伯超,南沙令荀仲举等。
侯景叛梁后地界齐梁的北兖、青等州为齐军占领,故北兖州刺史萧祗、萧放父子,青州刺史萧退、萧慨父子,青州刺史明少遐等,相继北入高齐。诸葛颖及樊儒、樊子盖父子等也是在侯景之乱中入齐的。
另有谯州刺史、梁宗室萧泰(字世怡),侯景南攻建康时军过谯州城下,城陷被俘,“寻逃脱得免,至于江陵”,江陵陷落后奔齐。梁末入齐的还有梁宗室萧庄、萧悫,以及士人袁奭、朱才、江旰。

西魏攻围江陵时,梁元帝曾求救于齐。公元555年春,齐清河王高岳军抵义阳,江陵已陷,遂乘机南进掠地,梁郢州刺史陆法和率部降齐,北入邺城。
当时割据湘、郢地区的梁旧将王琳,亦奉表归齐,“遣兄子叔宝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以出质于齐的梁宗室萧庄为梁主。随陆法和、王琳入北的将士为数不少,如隋代以精通音乐著称的万宝常、父万大通,贞观名臣王珪父王颚。王颚为王僧辩之子,僧辩的两个弟弟僧智、僧愔,亦在此前奔齐。
此外还有江陵失陷时被虏北迁,后由周奔齐的著名文士颜之推。
《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五月”条,称侯景军队在三吴地区“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所谓北境,就是北齐。
“漂流”至北齐的梁民为数甚巨,其中有“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主要的还是被掠卖的普通百姓。
2、江陵俘虏的惨状
《梁书》卷五《元帝纪》承圣三年(554)十二月条:
“(西魏破江陵后)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南史》卷八《梁元帝纪》同,但前有“汝南王大封、尚书左仆射王褒以下,并为俘以归长安”句。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魏恭帝元年(554)十一月条:“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
在此之前,梁元帝已命人将宫中所藏14万卷典藏书籍尽数焚毁。
魏军所俘虏、籍没的江陵军民并不是全部被押解到了长安。

首先,“小弱者皆杀之”。
因为作为奴婢,老人和小孩不但不能役使,还要消费,是不具备使用价值的。
其次,破城之日正值冬月底,驱归长安则在最寒冷的腊月,当时又遇大雪天气,《通鉴》称当时江陵俘虏为“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
再次,西魏军入城之后,多有抢掠杀戮,不少人死于非命。
西魏破江陵后,“肆其残忍,多所诛夷”。《颜氏家训·兄弟篇》载:
“江陵王玄绍,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友爱。…及西台陷没,玄绍以形体魁梧,为兵所围;二弟争共抱持,各求代死,终不得解,遂并命尔。”
这是魏军残杀无辜之例。
《陈书》卷三二《孝行·殷不害传》:
“梁元帝立,以不害为中书郎,兼廷尉卿,因将家属(自建康)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于别所督战,失母所在。于时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冻死者填满沟堑。不害行哭道路,远近寻求,无所不至,遇见死人沟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阅视,举体冻湿,水浆不入口,号泣不辍声,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尸。…即于江陵权殡,与王褒、庾信俱入长安。”
这是因魏军驱逼“老弱冻死者填满沟堑”之例。
《法苑珠林》卷九一《赏罚篇·感应缘》引《冥祥记》云:
“梁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乱,丧失家口,惟余小男,年始数岁,躬自担抱,又著连枷,值雪涂不能前进。元晖逼令弃去,刘君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取,掷之雪中,杖拍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首,号叫断绝。辛苦顿弊,加以悲伤,数日而死。”
这是小弱被杀及梁俘因天气寒冻及路途劳顿致死之例。

《观我生赋》文学性的表述则是:
“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掠”。
3、士大夫笔下的北迁之旅
既然是“阖城为贱隶”,当然包括王公百官,以及平素大冠高履、玉树临风的士族子弟。
《周书·武帝纪》称“并虏其百官”,梁元帝时任给事黄门侍郎、领尚书左丞的沈炯,在描写其被俘入关经历的《归魂赋》中,则谓“总官司而就绁”,亦即诸官署成建制地成为囚虏。
赋中“托马首之西暮、随槛车而回辙”,“既缧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窥”句,表明沈炯在入关途中仍身遭械系。
上引《法苑珠林》中的那位刘姓士大夫,北迁途中亦身“著连枷”,处于西魏士兵的严厉监视之下。
沈炯入关后第三年,“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
《归魂赋》艺术地再现了他的入关之旅。
虽属文学性描述,其路线仍约略可见:
从江陵出发后,沿汉水北上,所谓“历沔汉之逶迤”;过襄阳,“望隆中之大宅,映岘首之沉碑”;既而循汉水支流“淯水”,中经西魏荆州治所“濮县”(今河南邓县),西折历淅州(今河南西峡),越武关而至商州(今陕西商县),然后出蓝田关,抵长安。
这是历史上长安与南阳、襄阳地区之间的一条著名通道,有“商洛道”、“武关道”等多种名称。
沈炯后来自关中南归,走的仍然是这条路线,所谓“出向来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唯心情迥异而已。

庾信《哀江南赋》中描述江陵俘虏入关途中之苦,所谓“秦中水黑,关上泥青”、“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虽各有典故,实际上也是对这条路线的形容。
4、南朝的致命打击
南朝以降,尽管门阀士族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南朝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对于江南侨旧高门,仍是适合于他们生存的土壤。
侯景之乱,“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在三吴地区的,或因兵祸“坐死仓猝”,或因饥馑“待命听终”,也蒙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当时相当一部分衣冠士人辗转逃到了江陵,侯景之乱平定后,江陵更是梁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第一流政治、社会精英和文化名流的荟萃地。
西魏破江陵,阖城被虏入关,对南朝门阀士族是致命的打击。
文化在门阀形成及维持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对于早已脱离其宗族乡里的侨姓高门尤其如此。
一个家族的文化是通过名流和佳子弟来代表和传承的,许多门阀家族中顶立门楣的核心人物,最有发展前途的佳子弟,如琅邪王氏的王褒,陈郡谢氏的谢贞,南阳庾氏的庾信,琅邪颜氏的颜之推、之仪兄弟,沛国刘氏的刘臻、刘瑴,都在西魏破江陵后入关,使他们在南方的家族或蒙受严重损失,甚或从此一蹶不振。
侯景之乱受损失较小的荆州大族,如移居江陵的南阳宗氏、庾氏、刘氏、乐氏,西魏破江陵时几乎是举宗北迁,乡国既失,人物流散,他们在原籍的宗族势力从此不复存在。
迁居襄阳已达七世的河东柳氏,其柳仲礼一门自梁末入北后,便回到了祖居地河东,从此告别了第二故乡襄阳。河东柳氏柳霞一门,之所以直至隋代仍家族势力不衰,则因江陵破后他们继续任职于北周附庸后梁萧詧政权,而且从梁至隋始终未脱离乡里。
梁元帝覆败后出家入周的南阳宗氏宗阙殆,周“朝省以名(即阙殆)文翰可观,元非玄侣”,希望他能还俗任官,但阙殆坚辞拒绝,除了宗教信仰以外,还因为他自叹“乡国殄丧,宗戚衰亡”,“京都丧乱,冠冕沦没,海内知识,零落殆尽”,已无心于仕宦。
《周书·王褒传》称王褒、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入北以后,因受到优惠的待遇,“忘其羁旅焉”。待遇优厚是真,“忘其羁旅”则不实,他们强烈的乡关之思,有他们亲笔写下的流传至今的诗赋为证。

随着梁陈之际南方文人学者的成批北入,以及南方图书典籍的损坏和北输,南朝的文化优势受到挑战,南北文化力量的对比开始改变。
陈朝人才开始显出竭蹶不继之势,这从当时最反映南北文化学术水平的使节交聘中也可看出。
《北齐书》卷二三《崔瞻传》称大宁元年(561,陈文帝天嘉二年),北齐崔瞻使陈,“瞻词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
其言外之意是陈朝已没有能够接待崔瞻的人才。
《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也记载了相类似的故事:
“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魏收抑扬之意明显可见。道衡入隋后曾任聘陈使主,本传称“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上引二例都出自北人的记载,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但这样的传说在陈朝之前的宋齐梁朝,却很少见到。
尽管魏收、薛道衡都是在北朝后期文学南朝化潮流中成长起来的北方文士,但他们在陈朝时敢于揶揄南朝文士,除了反映北朝文化自身的进步以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北文化力量对比的改变。
东魏北齐时邺下号称多士,他们又接纳了来自南朝的颜之推、萧悫、萧放、萧退、萧泰、诸葛颍、明少遐等南方第一流文士,力量自更壮大。
北周的文化基础最薄,但在梁陈之际一大批第一流的南方文士入关,包括当时南北文化学术界最负盛名的重量级人物王褒、庾信。

这些人的传记和诗赋文集,后人编次时往往归于北周,事实上他们也大都在北周生活了数十年之久,并终老于斯,而且在他们的长期影响下,北周的文学新生代也在成长。北周的文化实力还应加上附庸后梁为数不少的文学之士。总之,我们说梁陈之际的南人北迁,在南北文化力量的对比上严重削弱了南方的实力。
5、北朝的逆袭之机
梁陈之际入北南人对北朝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及制度方面,文化方面的影响又以文学最著。
《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将南北朝各自文学发展的高峰分别定位于南朝的齐永明、梁天监之际和北朝的魏太和、北齐天保之际,并分别列举了南北的代表人物,认为各为“一时之选”,南北文风虽互有异同,亦各有短长。
尽管《文学传序》忽略了南北朝文学之间先进与后起、摹仿与被摹仿的关系,但它认为北朝文学在高齐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与北齐相对的梁末、陈朝的文风,《文学传序》基本上是否定的,但这种否定主要是从文学的政治功能着眼,认为简文、湘东及徐陵、庾信的文体,“盖亦亡国之音”,如所周知,这反映的是《隋书》史臣所代表的唐初官方的意见。
北齐文学发达,作为统治阶层的北齐勋贵,对南方文士既无特别的需求,对其文学作品亦缺乏欣赏的修养。但北齐汉人文士对他们所崇尚、摹仿的南方文化则是认同的,因而颜之推入北,深为北齐名流祖珽、阳休之信重。
文林馆的成立,虽由祖珽具名奏立,颜之推和萧放实为发起人,颜之推还是文林馆的主持人之一。
梁末入北南士颜之推、萧悫、萧放、诸葛颍、萧慨、袁奭、江旰、朱才、荀仲举等,以及人北较早的南人徐之才,均被延入馆内。有论者指出,正是由南朝入北人士所咏诵的“齐梁遗响”,构成了北齐诗歌的主体,足见其影响之一斑。
如上所述,北周文士奇缺,尽管王褒、庾信入关之前,苏绰就曾诋河“洛阳后进”祖述江左的华靡文风,那是因为“关中根本没有能写这些华靡之文的文人”。

不独文学,典章制度方面的学者亦极缺乏,故西魏北周对文学之士求之若渴。
西魏破江陵,王褒等入关,宇文泰喜出望外:“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
后来陈霸先与西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北周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对于最负文名的王褒、庾信,始终坚持不放。王褒、庾信入关,南朝的文学、艺术风靡北周。
入北南人对关中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培养了以宇文宗室为首的关中勋贵子弟对当时最流行的南朝文学的兴趣。周世宗、高祖身边常有入北南朝文士的身影,王褒、庾信等与宇文氏宗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乃人所熟知。
北周致力耕战,法度严明,对宽缓的“梁法”颇不以为然,但宇文泰以降的北周统治者对南方文学之士却待若上宾,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西魏北周优礼入北南士,不仅是“对西魏政权粗陋的政教学术作一种点缀”,而且是通过他们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声望,挑战北齐特别是南朝的正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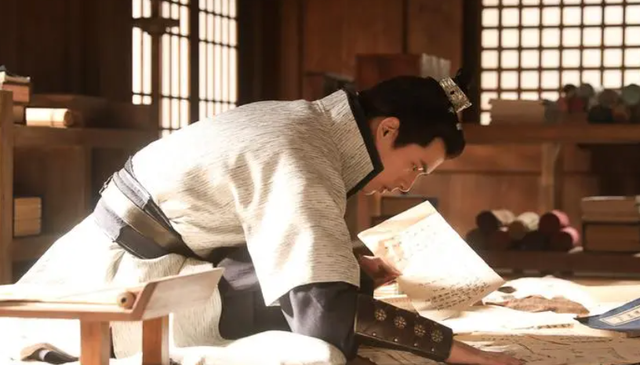
徐庾体诚然属于魏晋新兴文学的末流,但仍是当时文学的主流,落后的北周文坛引进了主流文学的代表人物,等于迎头赶上了早已风靡江左、邺都的最新文学潮流,使北周在文学上也能与江左、北齐争衡。
实际上较之出任文翰、书记之职,这才是入北南人对北周政治的最大影响。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