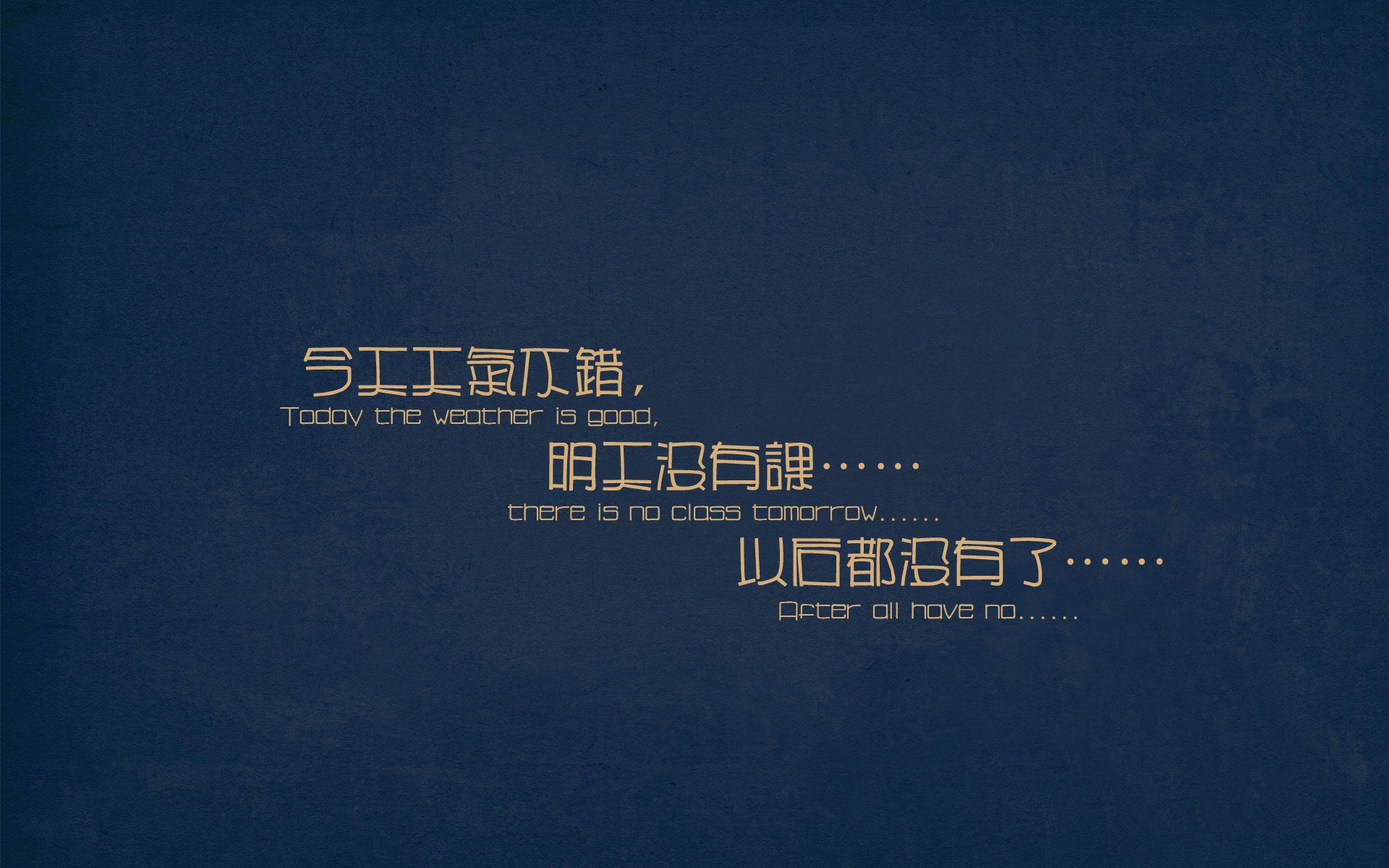【山西】薛振堂 |“火车头”军棉帽
- 旅游
- 19小时前
- 299
“火车头”军棉帽
作者:薛振堂
大雪节来临,时令已经是寒冬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
吃过早饭,我翻箱倒柜,寻找一些保暖的衣服。翻到箱底,一顶崭新的军用火车头面貌映入眼帘。军绿色的外表,鹅绒色的栽绒,正中还镶嵌着一枚鲜红色五角星。
捧起这顶火车头军棉帽,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当年的情景里。
这是2005年12月24日,我在北京参人民大会堂加完走进新世纪系列丛书《中华世纪坛》的出版发行暨表彰大会后,乘兴游览了八达岭长城。
这一天格外的寒冷,旅游大巴停在八达岭长城下,山里的寒风一阵阵袭来,冻得人牙关直打颤抖。停车场的西边,摆着各种防冷的衣服和用品,为了顺利登上长城游览,大家争先恐后地挑选着自己需要的衣物。我也和大家一样,加入这购物的队伍里。当时我的上身穿的是一件皮衣,下身穿着保暖裤子,只有头部没有保暖的用品。就在这时,那里摆放的一排火车头军绿色棉帽吸引了我,我大小就非常喜欢这样的棉帽子,就花了20元买了一顶。
大家穿戴好买好的保暖衣物,冒着凛冽的寒风,坐上缆车,很快就上到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长城上边的风,比起山沟里要大多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长城的雄伟壮丽和美丽景色。寒风中,一轮红日悬在东边的天空,放眼望去,风景这边独好,山峦叠嶂,云雾缭绕,草木繁盛,万里长城,崎岖蜿蜒,穿过云海,穿山越岭,一望无际。那一座座烽火台,错落有致,分布在长城的各处关隘,巍然挺立,雄伟壮丽。一队队中外游客,不顾刺骨的寒风,络绎不绝地奋勇往长城的最高处攀登,一睹这世界奇景。
我戴着刚买的火车头军绿棉帽,一点都不觉得寒冷。在攀登一个个台阶中,我默默地背诵着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和大家一起勇往直前。越到上边,寒风越大,也越冷,但是我的头上因为戴着这顶面冒,却暖和地直冒着热气,心里高兴,也是那么地暖暖的、热乎乎的。
我对这种样式的军绿色火车头棉帽是情有独钟的,也是深有感情和留恋的。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似乎冬天是个让人害怕的季节。那时候的冬天,感觉是非常地寒冷的。我们的小土巷道,都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大口子,整个一个冬天,各家各户的屋檐上都挂着长长的冰凌。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一双双小手都被冻得像一个个冰疙瘩,一道道血口子鲜血直流。每个人的脸,被寒风刮得刺下一条条血印,小小的头,被冻得肿起一块块疙瘩。没有像样的棉帽子,大人们想着各种办法,用土布给孩子们缝制了样式不同的棉帽,只要能够防寒就可以了,孩子们都不讲究是什么样是,什么颜色,什么布。
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文革的开展,军绿色在生活中时髦起来。也就在这个时期,火车头军绿棉帽也在农村兴起。那时候,小小的我们,对于这样一顶面帽也当作奢侈品了,很多人可望不可求。当时,我们只在电影里看见过解放军戴着这种栽绒棉帽,还有就是我们学习雷锋,看到过雷锋同志的照片也戴着这样的帽子,所以,在我们的幼小心灵里,能够拥有这么一顶军旅火车头棉帽,那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啊。
那一年冬天,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火车头棉帽子悄然在农村兴起。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清一色军绿色。样式五花八门,颜色各有不同。有栽绒的、有动物毛的,有蓝色的、有橘黄色的、还有东北人戴的那种样式的。但人们最喜欢的,还是这种军绿色栽绒的,中间镶嵌着一颗红五角星的军帽。
也就是这年的大雪节里,父亲去城里参加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顶军绿色栽绒的镶嵌着红五星的棉帽子。记得父亲是晚上从县城走回来的,我已经睡下了。父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乐呵呵地把这顶帽子给了我,当时我高兴地一夜搂着帽子睡不着。天不明,我就带着暖暖的棉帽子踏着大雪去上学。飘飘洒洒的白雪中,我头上的棉帽上的的那颗红五星格外醒目,我在大雪里大步向学校里跑去,要向同学们显摆显摆……
如今,人们在冬天里已经不习惯戴棉帽了,但是当年的情景永远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望着手中的这顶军绿色火车头棉帽,父爱的温暖永留心中,父爱的温馨永远永远在心中定格,再冷的天气里,也是那么的暖意融融。
百姓作家
应文友要求,《作家文学》开通作家专栏,旨在展示名家作品,推介优秀作者。
投稿注意:
投稿注意:投稿时,请精选5--8篇作品、创作心得与作者简介(100字以内)和生活照一起发邮箱,如有高清配图,可一并发来,请记得完善出生地。